《贵山漫记——旧事南明--茶馆·李妈》
作者: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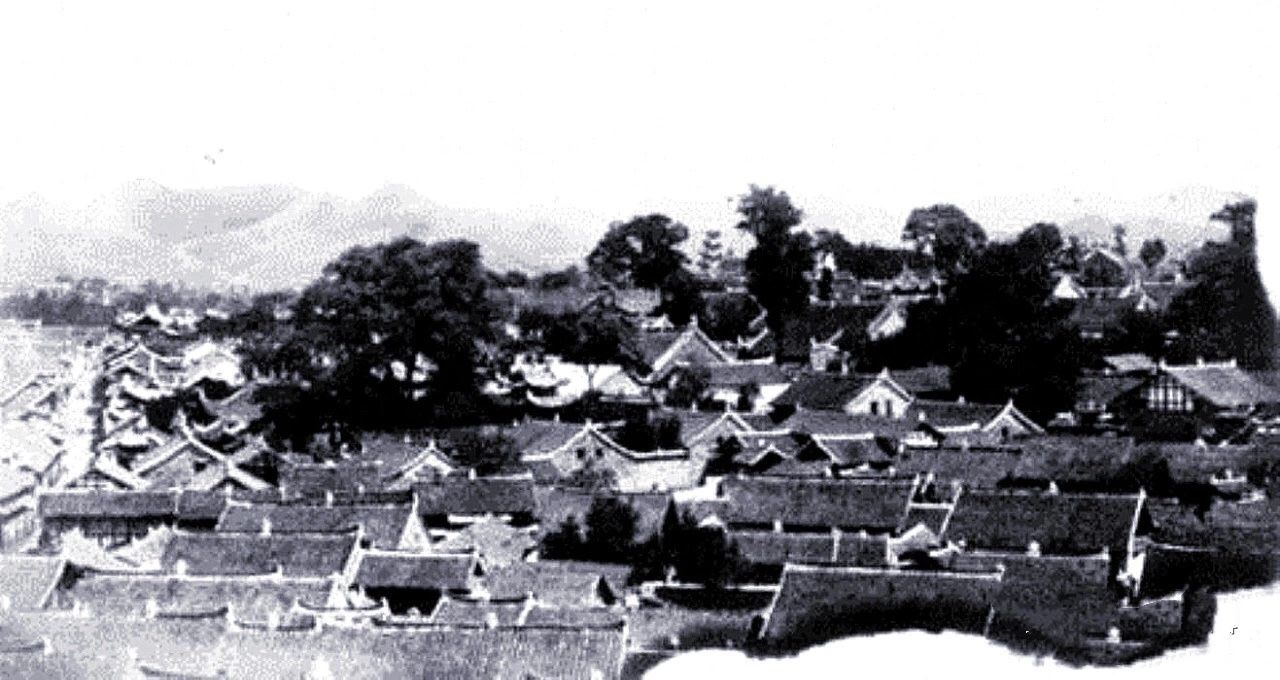
一
兴隆东巷的茶馆就是李妈家堂屋。抗战期间,“坐茶馆”成了新贵阳人(泛指抗战时期避难来到贵阳的人们)的一种特别嗜好,因此,他们怀想叨念故乡之时,茶馆是最解思乡愁之绝佳处。那时,贵阳的茶馆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兴隆东巷当然也不例外。
李妈茶馆的独特是外面的茶馆没法比的,因为她家每天都有盲人来说唱,说唱的尽是一些好听的故事,不论是大江南北的,还是地老天荒的,他们都能说得出来,更别提水浒、三国,孙悟空、林黛玉的了。
我们搬到兴隆东巷后,发现的第一个“乐游苑”,就是陆将军家后山坡上、杨家大河畔。那里有好几座从下往上依次排列的三层、五层、七层白石塔,还有好多有碑的无碑的、长满了乱草的荒冢;在那些疯长的野草中,竟然有一个“盲人工厂”。我每天都会看见三三两两的盲人相互搀扶着、说笑着从我家小后门、前大门经过。我与院子里的伙伴们时不时地会绕过几个山坡地去“盲人工厂”,看盲人们抬着或浑浊、或紧闭、或凹陷的眼睛,摸着一根根的铁丝,编织着一堆堆大大小小的漏瓢和一摞摞大中小号筛沙的筛子。每次我看见他们做工的样子,胸口就会疼,出不来气。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可他们还大声大气地笑着说话呢!
我看见来李妈茶馆唱曲的盲人中有些是“盲人工厂”的工人。一次,茶馆的跑堂小八桂叫一个盲人唱歌:“陈瞎儿,来一个‘拉手手’。”
这时,一个又高又瘦的盲人手拿着胡琴咿呀咿呀地调了调弦,张口就唱:
“你要拉我的手/ 我要亲你的口/ 拉手手/ 亲口口/ 我们两个旮旮里头走”
李妈出来吼:“鬼打的些哦,夜猫子嚎春呀!乱管唱,看派出所的不来抓你们去!”
李妈对于来茶馆的盲人吃茶是不收钱的,李妈让他们在茶馆里随便摆龙门阵,说是他们比我们苦,随他们。凡是唱曲的盲人,只要有人给钱,数下来超过2分,李妈就给他1分。我觉得李妈心真好。
我正发着呆呢,陈瞎儿又唱开了:
“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 瞎哥儿盼着那好光啊景/ 有朝一日翻了身/ 我和我的瞎妹子结个啊婚”
陈瞎儿一唱完,一片笑声、叫好声夹着几个嘣嘣嘣稀疏的钢镚声,陈瞎儿心满意足地坐了下来。
每天傍晚,当卖梨膏糖的小手风琴声响起,伴着那半瞎的老头与牵着他的小孩卖唱声亦起:
“梨膏糖呀/咕吱咕吱杠啊/楼下吃了嘛楼上香呀/咕吱咕吱杠”
听着一声比一声紧的“咕吱咕吱杠”,我的心也“咕吱咕吱杠”地催促着我。我知道,李妈茶馆的说书马上就要开始了。
叶子烟浓厚稠密的烟雾和焦苦刺鼻的烟味儿弥漫在李妈茶馆里,加上昏黄黄的灯光、竹靠椅、小方桌,还有大红桌、长条凳,白瓷盖碗、长嘴锡壶;再加上小八桂跑堂添水的应答、盲人的说唱讲古,时时都吸引着我。要不是怕妈妈生气,我是天天晚上都会去的。
李妈茶馆除了喝茶听曲外,还兼给巷子里的人们断公道。
记得是有一年的国庆节,巷子里一位郭姓教师好容易讨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花溪姑娘,在闹新房的时候,巷子里的人们都去凑热闹,有一群人将一个枕头放到新娘子手中,让她口里说着“哥哥抱起妹妹枕”,手里的枕头褥给新郎就行了。新娘将枕头褥给了新郎,就是不说话。那群人嘻嘻哈哈地声声催督着,新娘躲躲闪闪地就是不肯说。闹新房的人们推推攘攘地将俩新人褥做一堆,那新娘终于哭开了,挣脱着跑了出去。这下还了得,新娘子跑的方向正是杨家大河。大家拼命地追着喊着。李妈猛然大声喊道:
“都不要追了,小八桂,你抵柱跑,先把新娘子稳住;郭老师,你跟我一块去。其他的人,不准来!”小八桂大步飞奔,李妈在后面紧跟。最后,在河边,小八桂先拦住了正要跳河的新娘子。
李妈紧一步抱住了新娘子,手轻轻地拍着新娘子的背,嘴里不停地:“幺儿,幺儿!乖啦!莫哭,莫哭啦!没得事,没得事了。”
李妈殷殷地哄着新娘子,郭老师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李妈将新娘子身子扳转过来,交给郭老师,郭老师拉着新娘子的手,俩人哭了好半天。
李妈将起哄闹新房最过分的那几个青头呼到茶馆,让郭老师大胆地说他们,让新娘子出气,还说愿打愿罚任随他俩。郭老师喏喏着开不了腔,新娘子更是死活不转身。李妈急得大口大口地猛喝茶,最后,又找到我妈妈,妈妈只好来到茶馆解决此事。妈妈说结婚闹新房是好事,邻里乡亲大家欢欢喜喜的,但要有个度,不能逾越了尺度。
那伙青头齐齐问:“哪样叫尺度?”
妈妈笑笑说:“就是准则、法度的意思。古时候就有‘丈夫治田有亩数,妇人织紝有尺度’的说法。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什么事都要把握分寸,闹新房也一样要讲究分寸。”
看那伙人大眼瞪小眼地杵在那儿,墨者黑也地坏笑着。我小弟开了黄腔:“猪猡些!过分懂不懂?文盲加流氓,一肚子粪坑!快,排好队,一个一个地给新娘子鞠躬。”
真是“一行服一行,萝卜服米汤”。那伙青头竟规规矩矩地依次序给新娘子鞠躬道歉。李妈虽还在恨恨的,但还是让他们离开了。
二
李妈是兴隆东巷居委会副委员,由于她古道热肠,老幼和三班的,谁家有事,她都第一个到场帮你排忧解难,所以巷子里人人都喜欢她。不叫她“李委员”,倒叫她“茶馆李妈”。
李妈的茶馆是兴隆东巷“摆龙门阵”的聚居地。好些个抗战时期在此地定居的外乡人都爱聚集在茶馆里,不同的口音诉说着相同的思乡之情。常常是吃一颗酥黄豆滴一滴思乡泪。有一回“鬼节”,家家户户都在各家门口烧纸钱。我们院子里的重庆人井老师还未烧完手中的纸钱,就哽咽着跑到李妈茶馆里,唱起了一首很好听的抗日歌曲:
月儿高挂在天上/ 光明照耀四方/ 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 记起了我的故乡//
半夜里炮声骤响/ 火光布满四飞/ 我独自逃出了敌人手/ 到如今东西流浪……//
一向唯唯诺诺的井老师流泪抹眼激情澎湃地高唱着,全然没有了平常的羸弱相。全茶馆的人都被井老师感动了,个个屏住呼吸,有的还流着泪;大家庄重肃穆地看着井老师,连门外呛人的香蜡纸烛臭烟味都没能呛醒大家。这情景真是让你想忘都忘不掉。
李妈茶馆也常常有巷子外的茶客来饮茶,说是喜欢李妈茶馆的酥黄豆,酥脆酥脆的;还有五香豆腐干颗颗,香绵香绵的。有一次我姐姐的高班同学、李妈的女儿小秋,从荷包里掏什么东西给我姐姐,两人一块吃的时候,正巧看见我打酱油回来,顺手给了我一小把;我惊喜地发现,小秋给我的那一小把东西,里面竟有酥黄豆,还有五香豆腐干颗颗。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酥黄豆和五香豆腐干颗颗。
李妈茶馆里泡茶、跑堂的都是小八桂。李妈说小八桂手勤脚快的,还忠诚可靠。陈嬢嬢说小八桂其实可以进工厂工作的,但他既不能也不想离开茶馆。不能离开是小八桂的父母年纪大了,还都生着病,时刻离不开独生儿子;不想离开就是小八桂喜欢李妈家小秋。自从抗战时期小八桂家从广西逃难搬进兴隆东巷后,就与李妈家两对门住着,两小孩年龄相当,亲梅竹马的,渐渐就有了相互喜欢的情愫。
小八桂觉得李妈是嫌他家没有根基,说其实他家在广西有大片的桂花树林,还昂声昂气地唱念起:
“中亭地白树栖鸦,冷霜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念完后,一向粗声大气的小八桂竟幽幽地叹了句:“哎!只可惜现在回不去了。”
李妈茶馆的茶叶都是清一色的“赵司茶”。听我妈妈说,“赵司茶”是花溪黔陶赵司村出产的“贡茶”,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清康熙年间,贵阳进士、著名学者、诗人周渔璜曾以花溪赵司茶进贡,康熙皇帝品尝后连说三声“好”,而后赵司茶就有了“品尝周公赵司茶,皇宫内外十里香”的佳话。
在李妈茶馆喝茶,2分钱一盏的盖碗茶,慢慢品就,想坐多久就坐多久;若你有事离开,只需将茶盖斜放在茶托上,小八桂就会给你保留。其实,即令是1分钱一杯的大众花茶,李妈也从不撵人。
李妈茶馆赚不赚钱李妈其实不在乎,她在乎的是天天有人来她家吃茶,她觉得实在。李妈丈夫离家多年没有回来,李妈开这个茶馆就是为了等丈夫归家时找得到家。
可惜直到李妈茶馆在“文革”初期被勒令关张时,她的丈夫仍然没有归来,李妈也不知道疏散下放去了何方。而小八桂与小秋最后是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终究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