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90.0悦读 | 《黄庭坚故事》:与水结缘的山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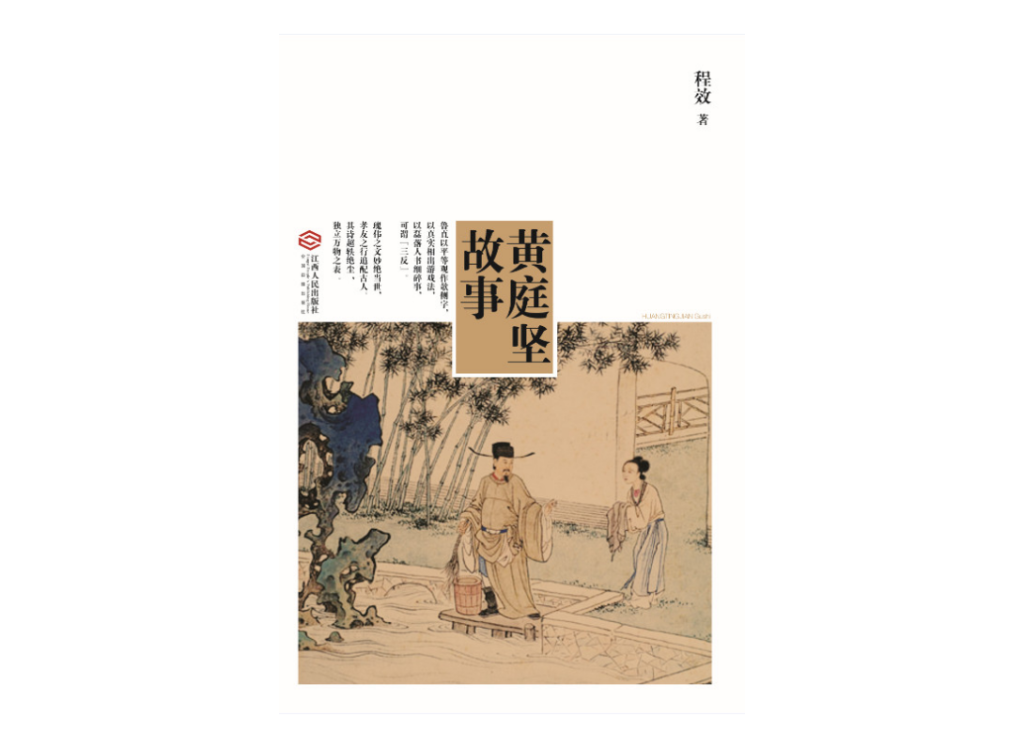
程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源于幕阜山麓的修河逶迤东流,绕群山而纳溪流,穿村庄而环集镇,汇聚成一条横贯赣西北地域,流经修水、武宁、永修三县,奔流达七百华里的泱泱大河。
从修水县(今江西修水)城以西乘船溯流而上,航行过碧波荡漾的十里秀水,便抵达闻名遐迩的千年古村——双井村(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杭口镇下辖村)。坐落于明月湾畔的双井村,缘于临河的两口并排的水井而得名。
居高远眺,村北的杭山连绵起伏,披绿叠翠;村南的修河流淌,清澈透底。江西诗派的开山宗师黄庭坚故居,就坐落在巍峨的杭山脚下,历来被人们称为“黄家堂屋”或“山谷故居”。
距今970多年前,北宋文坛一代巨擘黄庭坚,就诞生在山清水秀的双井村。正是这位当年“神童”的横空出世和他60余年的人生所铸就的辉煌,使双井这样一个原本默默无闻、偏僻闭塞的村落,一举成名天下知,至今仍是修水县一张烫金的历史文化名片。
透过历史的烟雨尘埃,从茫茫史海中寻觅山谷先生的一个个人生片断,在其生平故事每一个起承转合的节点,我们似乎都能清晰地听到或看到:一条亘古流淌的大河淙淙的水声或时隐时现的桨声帆影。这就是江西五大河流之一的修水。
山谷先生一生起点和终点与修河紧紧相依。他的人生起点在修水明月湾畔的双井。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度过了年幼入馆求学和以“神童”见称乡里的一段天真快乐时光,清澈的修河水滋养和抚育了他成长。历经人生的起伏,仕途的坎坷,晚年他客死广西宜州,其灵柩最后在两位生前好友的护送下,长途跋涉,水陆兼行,经陆路入分宁县境,从修河上游的一段下船,才回到双井故里,归葬于黄家祖墓之西。在他人生谢幕的终点站,山谷先生紧紧依恋着他深爱的慈母,长眠于依山傍水的故土,听松风,饮甘露,与双井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相依相伴,千百年来受人景仰。
山谷先生一生与“水”有缘。年幼时,双井的山流小溪、村中大若池塘和临河的钓矶,都留下过他读书的身影和玩耍的足迹。年少遇父丧,他随舅父从修河顺流东下,出烟波浩渺的鄱阳湖而转入浪潮奔涌的长江,平生第一次走出了故乡,走出了州府,抵达淮河之南的涟水游学。他在这里求学,在这里成家立业,后来他携发妻逆向沿相同水路返回故里,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成长为博学多才的青年俊彦。
到了青壮年时期,无论是参加科举考试、辗转各地做官,还是回乡探亲访友,从修水出鄱阳湖转长江,或者从相同路线逆向返回。这条相对固定或者说必经的人生主航线,他不知道来往奔波了多少回。在地图上搜寻他一生的行迹,在这段主航路线加长伸展的另一段,则是从扬州经大运河、抵汴水至大宋的京城汴梁。从第一次赴汴梁应试算起,他从东京汴梁沿这条水道南下北归的次数多得无法准确统计。印象最深的是他曾经从京城出发,三次渡过黄河,先后做过叶县尉、北京大名府教授、德州德平镇知监三任地方官。其间有一段小插曲:他在赣江之滨的太和(今泰和县)还做过一任“吏不悦,而民安之”的县令。在他任地方官这一时期,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愈演愈烈,虽然他政治上倾向旧党,但在任下层地方官时,对王安石新法中的“农田水利法”,采取“择善而从”的态度,在自己管辖的县、镇,大力兴修水利,治理河道和加固护堤,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办了大量的实事、好事,被誉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
山谷先生一生的坎坷与“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他出仕之初即遭受挫折,主要是汝水上涨而道路阻断,以至因为迟到而被上司拘禁,也许这与“水”有关的当头棒喝,在他一生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到了暮年,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他两遭贬谪都与“水”相关。一次是主修的《神宗实录》中“用铁龙爪治水有如儿戏”的据实记载,被政敌攻击为“修史不实”,他被贬谪偏远的巴蜀之地。在这七年之中,无论是艰难跋涉西入蜀川,还是后来遇赦东返,他的行迹大致在长江上游到中下游流域辗转徘徊,一度寄寓在江汉流域的州县。另一次他在江陵为人作《承天院塔记》的碑文,文中提到国家的财力不应过多消耗在建寺庙道观,而是应多花费在治理水涝灾害方面。不料又被政敌从文字上断章取义,罗织了一个“幸灾谤国”的罪名,朝廷革去了他的官身,放逐广西宜州。山谷先生不得不从江汉流域出发,经长江而入洞庭,渡过三湘之水,以及桂水、榕江,最后被羁管于龙水之滨的宜州,客死在城南一个狭小的戍楼里。
也许有人会说:水是生命之源。最早的人类祖先大多是逐水而居,故华夏大地上的古城老镇大都崛起于江河之滨。所以,黄庭坚一生的行迹与江河湖泊紧密相关算不上稀奇。然而,仅以他一生中的羁旅行役时段来统计,他借助舟船行走的时间总和,肯定超过了他在陆地行走的时间总和,这在有宋一代诗人中是不多见的。当人们读过山谷先生大批量的传世诗文作品后,无不会惊奇地发现:山谷先生的诗词创作,几乎是无水不出诗篇佳句,无江河不出诗词力作。诸如“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鄂州南楼书事》)、“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夜发分宁寄杜涧叟》)、“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水调歌头·游览》),等等,都是历代诗词选本常选的名篇和人们交口传诵的名句。由此可以说,山谷先生出生在修河之滨,饮纯净的修河之水长大,水赋予了他先天艺术灵感,水浸润了他艺术的心田,溶进了他生命的血液,成为了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动力和源泉。
纵览山谷先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无论是作为诗人、词人,还是作为官员,抑或被流放羁管,我们通过剪裁史料而串联起来的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都可以看到一个兼融儒、道、释的谦谦君子,一个正直儒士积极出世的政治追求与遁世相交织的心理积淀,都可以看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双向追寻,都可以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都可以看到匡扶社稷、救济苍生的家国情怀。
山谷先生60余年的人生,虽说不上是一个特别惊心动魄的过程。历史上如他这般才高八斗、贤良正直而仕途坎坷、沉沦下僚的志士仁人并不在少数;他所经受的年少丧父、两失妻室的惨痛和两遭贬谪的磨难以及客死异乡的结局,并非绝无仅有,但唯独他以豁达的襟怀和高尚的道德操守,赢得了很高的生前身后名,并以崇高的文学成就而被尊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身后享有尊崇无比的“文节公”谥号,还因“涤亲溺器”的孝母之举而被列名历史上的“二十四孝”之一。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也许在山的博大和水的平静相比较中,我们更看重水的灵动和深邃。往事越千年,世事如流水,山谷先生一生与水结缘,可以说一如泾渭分明是其人生取舍的标尺;上善若水,流水不争,山谷先生毕生眷恋家乡那条母亲河,纯净如水是其人格的最高显示。
最后,不论你是否接受该书在讲述一个个鲜活故事的同时,穿插着对山谷先生及其文学创作成就作出的高度概括和评价,只要你静下心来,品读这些既可独立成篇,又可构成有机整体的一组组故事,徜徉在山谷先生诗文营造的浓郁艺术情境之中,你一定可以借助想象的翅膀,穿越岁月的时空,真正读懂山谷先生的人生情怀、理想追求、知识结构和生命印记,还可获得多方位、广角度和深层次的艺术感受,从而拉近与这位逝去900多年、杰出文学艺术大师的生命、感情和作品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