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红色贵阳 | 为了原子弹爆炸,我来到罗布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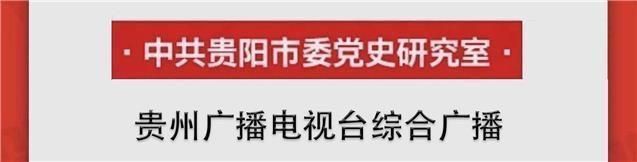
贵阳市鲤鱼村的一栋单元楼房,住着一位思维敏捷、精神矍铄的九旬老人,他叫陈树清。
只要提起“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陈树清可以一口气说出那天他在罗布泊的行程。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回忆起亲历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他依然激动不已。
讲述人:陈树清,94岁,贵州省人民政府退休干部,1964年在罗布泊720兵站担任作战参谋。

陈树清
保密:家信不超100字
1964年10月16日一大早,我和部队的战士们,就被带到罗布泊的一个地下掩体,这里距离原子弹的爆炸地点有10公里左右,属于安全地带。这样的地下掩体有很多个,我所在的这个地下掩体,在地表5米以下,长方形,可以容纳20多个战士挤在一起。等待原子弹爆炸这一天,我们已经在罗布泊待了5年。
1949年11月,我家住在贵阳火石坡(现延安东路与宝山北路交界处)。贵阳解放后,我报名参加解放军,当了一名汽车兵,把汽车从贵阳开到西藏。1959年6月,我突然接到通知,部队让我到洛阳学习。学习的内容全是保密规定,我也不知道为啥学习这些内容,反正听从指挥就行。两个月后,部队要从洛阳出发,让我们给家里写信。信的内容不能超过100个字,我按照规定,只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一切都好,勿念。”之后,寄给在贵阳的父母。
跟随部队,火车转汽车,也不知走了多久,我们到达了一片荒漠,听驻守在这里部队战士说,这里叫罗布泊。此刻我才知道,这里是我国试验原子弹的地方。尽管好奇心冲上大脑,严格的保密制度摆在那里:“知者不说、不知者不问、办公室之间不能互相走动。”我的职责就是给首长开好车,掌握好方向盘,确保首长的安全。我开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改装的客车,有几次,张爱萍将军都在这辆车上开会。
我们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代号叫720兵站,地上是帐篷,地下是掩体。掩体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光是门就有1吨重,里面通水电,摆放有办公桌,还有一个扩音喇叭,保持和整个基地的联系。
我们部队所在的这个生活点,叫马兰村。这个名字,是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取的。1958年,西出阳关的张蕴钰率领人员在戈壁滩上寻找核试验的场地时,选中了罗布泊。他看见一条天然水沟边长满了马兰草,就取了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电影厂:遥控拍摄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是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起爆前,我们把用作试验的废旧飞机、坦克、高射炮、火车头等,运到距离起爆点较近的地方,用于检测原子弹爆炸时的能量。在基地多年的工作中,我知道原子弹爆炸的瞬间,温度有25000度,相当于太阳核心区的温度。原子弹爆炸时会产生冲击波、核辐射、光辐射,还好我们在地下掩体隐蔽,比较安全。原子弹爆炸后,指挥部确认了安全,在地下掩体的扩音喇叭中通知大家,可以走上地面了,我们闻讯后欢呼不已。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军人走出地下掩体庆贺
原子弹爆炸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摄纪录片。摄影师和部队多次商量,反复调试,把摄影机安在了距离爆炸中心10公里左右的地方,采用遥控的方式进行拍摄。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蘑菇云,就是这样拍摄出来的。摄影师拍摄完毕后,第一时间乘坐张爱萍将军回京汇报的专机直飞北京,把电影胶卷冲洗出来。
在地面,我看到,爆炸点附近,高达105米的铁塔,在爆炸造成的高温下都化成了铁水,火车头、坦克、飞机等被爆炸时的能量掀了个人仰马翻。
后来,我听战友说起,在距离爆炸点中心大约10公里的前线指挥室,10分钟、9分钟、8分钟……倒计时的过程扣人心弦。然而,在距离正式爆炸还有90秒时,控制室发电机突然停了,负责无线电通信的战士望开德把交流电闸转接直流供电,保证了报时声音正常发出。由于报时准确无误,现场的指挥人员戴好护目镜,避免爆炸时的强光对眼睛造成伤害。
1970年1月,我从部队转业,回到故乡贵阳,进入贵州省人民政府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