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空间·叙谈录丨蔡崇达:建一座故乡的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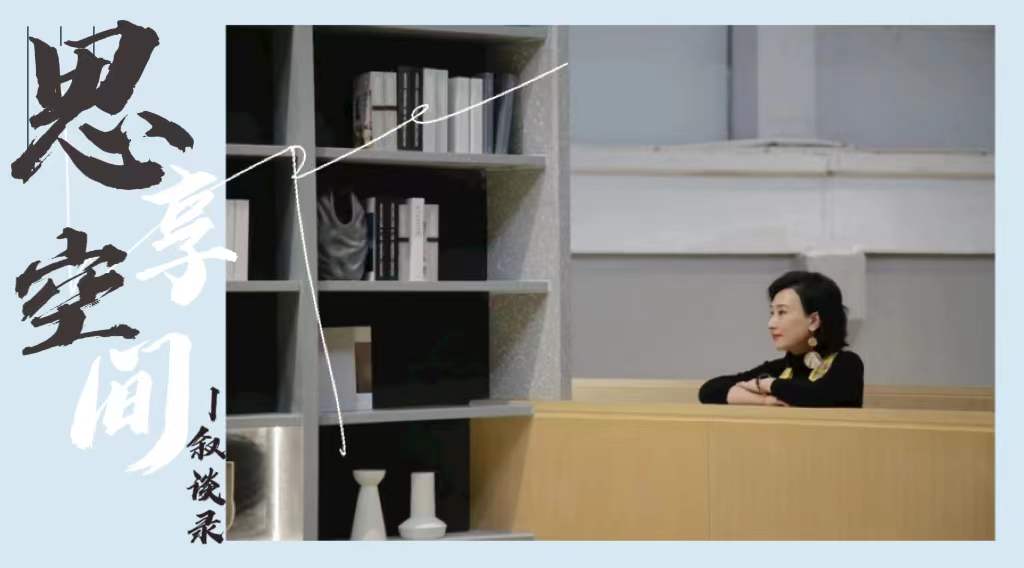
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是蔡崇达喜欢的一句话。阅读曾是他年少时的避难所,他说,小时候做梦都想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躺着、坐着、趴着,看一日又一日的书,空间安静,阅读自由。
当他的小说《皮囊》销量突破300万册,蔡崇达决定将老家的房子建成一座对外开放的公益图书馆。这老家的房子便是他《皮囊》书里的那一座《母亲的房子》。

东石的小镇很挤,弯弯曲曲,一边是大海,一边是街巷,有人为家乡铺路,有人为家乡建楼。小镇的人们亲切地挨在一起住下,人们的心啊,总在鸡犬相闻的夹缝处,惦记着一份清寂,若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人们在这里沉思、丰盛、共鸣、成长,那该多好。
他说,“还未有人为小镇建一座公益的图书馆,我是作家,我来做很适合。”
他小镇里的家,在巷子的深处,母亲建下的4层楼房有粉红色的外墙砖拼贴,是上个世纪末的风格。一家人生活在上海,这座房子也就落寞了起来,一年住进来的次数屈指可数,便不再另寻他处,就将家园进行改造。
“母亲的房子”图书馆。这个名字开始于个人私密的情感,但最终完成的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
 改造前的故乡老房
改造前的故乡老房
为了建这座图书馆,母亲的房子要被拆掉重来。
听说要回去建图书馆,母亲刚开始很开心。可当蔡崇达开始频繁地与设计师对接细节时,她却又伤心了起来。
那房子,大门的石头对联,是父亲送给母亲为数不多的惊喜,他将两个人的名字编入对联,刻在石头上;屋子里有他们结婚的床,掉了漆,可却都是留有记忆的。母亲难过,“推倒了就没有了……”
在《皮囊》的书中蔡崇达曾写过,为了建这座房子而疯狂偏执的母亲,她在父亲中风偏瘫,生活困顿到去捡拾人家扔掉的菜叶时,两度头也不回地浪费钱去盖一座会被拆迁的房子。
这是一个很难被人理解的母亲,但只有读到最末的人才知道,母亲盖的不是房子,是父亲与她空地上画地而起的爱情。这房子,是她一生的信念和圆满。
一位看过这本书的朋友说,她流得最多的眼泪,是在这一个章节里。
这一座建成不过十数年的房子,对蔡崇达的母亲而言,是一座特别的家园,不是轻易就可以告别的房子,她心情被拉扯着,忽高忽低。
直到最后听说,设计师会将石头对联、掉漆的床都保留下来,落成之后的空间,也许将成为一座地标,她才又开心了起来。
房子动土。在闽南人的习俗里,动土是件大事,母亲特地回到东石,操持动土仪式,和老房子做了一番告别。怕母亲触景伤情,仪式过后,蔡崇达催着母亲赶回上海。
 改造后的故乡图书馆
改造后的故乡图书馆
做一家公益图书馆是一个浪漫的梦想。但实现梦想的过程是艰辛的,蔡崇达说,只有他一个人是不够的,庆幸有许多人与他一起。
这座为小镇而建的图书馆,小镇上的人只需凭有效身份证,就可以借出一本书;小镇外的人同样借书免费,只需要付一定的押金。图书馆的运营由他在东石母校的校长来协助,日常管理则由学校文学社的社员们来帮忙。
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十一年前曾写过一本《纯真博物馆》的小说:男主角凯末尔用了十五年时间,收集着心上人芙颂摸过的所有物品。在现实世界里,帕慕克建造了一个真实版的“纯真博物馆”,书上出现的物件,被一件件陈设在博物馆里。
这座博物馆每年迎接着,全世界带着这本书,寻访而来的人。书迷们排着队,在书上的内页留下博物馆的“蝴蝶印章”,好像一定要来到这里,亲眼看看这座博物馆,这本书才算读完。伊斯坦布尔,也因这座博物馆变成了一个特别的城市。
相同地,这座“母亲的房子”,就像是《皮囊》读者心中“所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它像纯真博物馆一样,保留了这本书里所有的痕迹。
未来,这座“母亲的房子”图书馆也将变得特别起来,甚至连这个东石小镇,都将继续发生着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
文本参考:2040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