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科学家故事 】任继周和他的贵州知己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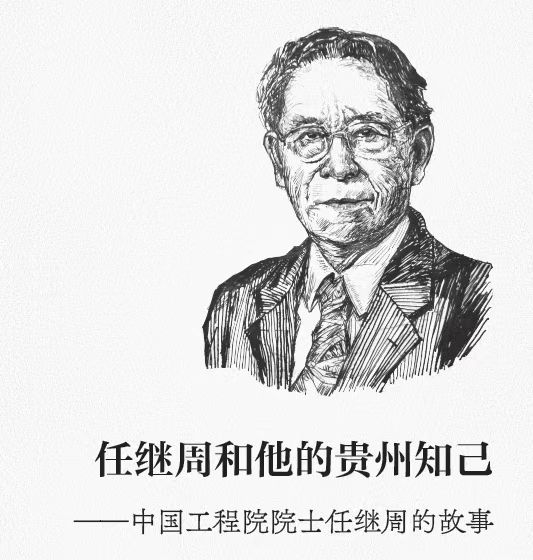
任继周(1924.11.7— ),男,山东平原人。草地农业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带领团队在贵州从事草业研究,为贵州草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任继周为治理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带领科研团队成功建立 了“威宁高原草地试验 站”和“灼圃联户示范牧场”,此后又进一步打造、推广了具有贵州特色的“独山模 式 ”“晴隆模 式 ”“长顺 模式”。
草是灵性之物,只有融入它的生命里,才能听见它的声音,读懂它的语言,看到它春萌秋萎、枯荣过后的美丽。任继周就是这样一位与草结缘的草地农业科学家,可他却调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草人”。如今他已经98 岁了,却仍时不时想起当年在贵州的经历, 想起贵州的知己——贵州省农业厅原厅长赵庆儒。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我国西部农村“以粮为纲”的思维模式还处于主导地位。对于贵州这样一个没有平原支撑、境内喀斯特地貌面积10万多平方千米,且石漠化严重的省份要不要发展草地畜牧业,专家们曾一度开展过激烈争论。有坚持“以粮为纲”的,也有主张发展林业的。可现实是,由于农民粗放式的种植方式,收入低不说,还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加速了石漠化。走“以粮为纲”的老路显然行不通,倘若弃农改林,农民生活又会没有着落。 所以,任继周认为,发展草地畜牧业,既可让农民在原有基础上安居乐业,又能改善水土流失。
但在当时,任继周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同。1982年10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贵州召开。会上,任继周第一次敞开心扉,大胆地坦陈了他对传统农业系统的批评意见,并阐明发展草地农业的可行性。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的发言得到了农业部门很多人的高度赞同,其中包括时任贵州省农业厅厅长的赵庆儒。
会后,赵庆儒主动找到任继周,围绕贵州能否发展草业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没想到两人十分投机。任继周很是感慨:“在全国的农业厅长 普遍只为粮食奔忙的时代,赵庆儒却能独具慧眼,重视草地,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在不同场合,任继周都称赵庆儒是既要管粮食,又要管草地、畜牧、研发、培训的 “大农业厅长 ”。就这样,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因发展草业观念的高度契合而走到了一起,成为相见恨晚的知己。
赵庆儒,1928年1月生于河南南乐,1944年1月进入冀鲁豫边区抗日一中学习,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3月随军南下。先后任团贵州省委青农部部长,安顺地委副书记,贵州省党组书记、农业厅厅长,以及贵州省委委员等职。他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领导,第一次听任继周关于草地农业的学术报告就产生了强烈共鸣。任继周的观点打开了他的思路,让他看到了贵州草地发展的广阔前景。作为贵州农口部门的“掌门人”,赵庆儒觉得为任继周在贵州的科研工作保驾护航,自己义不容辞。
事实上,任继周也并非一时冲动,他是在借鉴新西兰、澳大利亚牧草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考察了除了黔东南以外的大半个贵州后,才得出的结论。有了赵厅长的支持,他在贵州的调研就更顺利了。大会结束的第二天,赵庆儒就专门为任继周安排了一个小型考察队,队员2名,吉普车2辆,由当时的农业厅副厅长潘介农全程陪同。
那次考察前后共6天时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虽然辛劳,但收获满满。通过考察,任继周发现贵州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 尤其水热资源比北方还丰富。但发展短板是日照不足,发展粮食生产优势不明显,大部分地区属于岩溶山区,加上农民长时间不科学地耕作,石漠化问题日益突出。任继周认为,贵州的贫困程度虽然在全国“数一数二”,但自然条件与新西兰相比并不逊色,发展草地畜牧业大有天地。
任继周团队考察归来后,在赵庆儒的要求下,贵州省政府专门组织了一场“任继周贵州山地考察报告会 ”。会上,任继周结合农业生产中的问题,畅谈了实地考察的感受。这是一次颇具规模的大会,全省有关部门数百人参加,大礼堂被挤得满满当当。这让任继周无比兴奋,那积压多年的对中国农业科学发展的拳拳之心终于爆发。他甚至大胆地提出:如果畜牧业产值达不到农业总产值的50%,我国农业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这一观点振聋发聩,但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粮食不过关不能发展畜牧业”的说法早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会后,任继周有些忐忑不安。没承想 他署名的文章《关于我国南方建立草地农业系统的问题》第二天就在省委机关报《贵州日报》全文刊出。任继周激动万分,他在感谢贵州省党政领导的认可和支持的同时,更佩服赵庆儒的勇气和担当,能够将发言稿完整地呈送给贵州省委、省政府。
任继周就这样与贵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六五”到“十五”的5个“五年计划”时期,再到落实一批国际援助项目,他和他的科研团队将 25 年的时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贵州草业。此后许多年,他还念念不忘赵庆儒,念念不忘贵州的高山草地,念念不忘威宁试验站所在地——灼圃。
灼圃位于威宁雪山镇(曾称狗街乡)境内。当地早年流传过这样一首民谣:“灼圃狗街子,苦荞粑粑过日子。想吃包谷饭,要等老婆坐月子;想吃大米饭,除非到了下辈子……”可见当时老百姓的日子是何等穷困!
任继周第一次到灼圃考察时,发现这里虽然贫瘠,但地貌特征和新西兰草原的十分接近,可以借鉴甘肃马营沟试验站成功经验,在灼圃再建一个站点。他甚至设想,等草地发展了,再把当地农民动员进来,开展畜牧业养殖,以科技带动农户,一定会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赵庆儒,立即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
恰巧那时正在开展的“鄂、湘、黔三省南方草地试验示范区项目”已接近尾声,任继周担心“项目结束之日就是项目死亡之时”的老问题再次出现,于是坚定地提出建立自我维持的经济实体和试验站。让试验站为经济实体提供持续性的科技支撑,再让经济实体反哺试验站,使科研与生产互惠互利,良性循环。 这个意见很快被农业部草原处和贵州省农业厅采纳, 当即决定建立试验站,由贵州省农业厅与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合办,启动资金从“鄂、湘、黔三省南方草地试验示范区项目”经费中挤出。根据任继周的建议, 建站地点就选在了威宁气象站供电系统附近,便于工 作开展。
灼圃试验站建立之初,条件十分艰苦,任继周和他的科研团队吃的是洋芋、包谷、糙米饭,住的是石头和水泥砖垒砌的房子,就连用水也要走很远的山路才能取到。赵庆儒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带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建站基地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在贵州省农业厅的大力支持下,威宁高原草地试验站如期挂牌,首任站长由任继周的学生蒋文兰担任。 从此,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贵州山地试验站和灼圃试验示范牧场诞生了。
1985年7月27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参观灼圃,为他介绍牧场情况的正是试验站站长蒋文兰。她汇报道:“这里比西北好,适合养羊,经济效益稳定。羊毛市价五元一斤,西北却要十元。威宁老百姓会养羊,羊毛销路好。”胡锦涛同志听了很高兴,当即对县委同志作出指示:要鼓励群众积极养羊。
随着工作的深入,试验站又与当地政府合办了灼圃示范牧场,同时吸收 6 家专业大户,给予贷款扶持, 让他们共同建设和管理草地,开展畜牧业营运。不久, 又联合组建了经济实体“灼圃联户示范牧场”,又发展 了 9 家专业大户。

由于牧场发展顺利,农户很快还清了贷款,先前的贫困户发展成收入较高的富裕户。此后又有多家农户申请加入,影响越来越大。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脱贫致富的“灼圃模式”。
任继周和他的学生蒋文兰、李向林等一批科研工作者,在贵州开展的一系列山地草原科研攻关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过程充满艰辛,但他们乐在其中。李向林在回忆那段经历时说:“那时任老70多岁了,精神很好,外出考察走山路,年轻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任继周一直热爱贵州,贵州的一山一水、一 草一木都让他无法忘怀,他感谢这片土地,感谢同他合作过的许多人,尤其是他的贵州知己赵庆儒。
如今,已近期颐之年的任继周,每每忆起赵庆儒, 都会感慨不已,正如他在《大农业厅长赵庆儒》一文中所写:“庆儒同志走过的这 74 年的人生,是光辉而崇高的。我为有这样一位挚友而感到幸运和自豪。”应该说, 任继周、赵庆儒,以及蒋文兰、李向林等,都是懂草、爱草、敬草之人,他们为贵州的草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的灼圃牧场经过若干代人的精心打造,一直在不断地延伸、扩大,面积已达到上万亩。它延绵起伏,像一片绿色海洋,荡漾在贵州高原上。
【点评 】一个是热爱草地农业,俯下身子,面向土地,一心一意为改变贵州山区落后面貌,将几十年时光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贵州草业的科学家;一个是知才、惜才、爱才,并且敢于担当,尊重科学的领导干部,因共同的事业追求,共同的崇高目标,结下革命的友谊,两人的友谊令人羡慕和感动。
什么是知己?即思想上互相欣赏、心灵上互相共鸣。任继周、赵庆儒坚持科学报国,以拳拳之心,为贵州的脱贫减贫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之路,他们是铮铮铁骨铸就家国情,他们是“中国的脊梁”!
来源:贵州科技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