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苗族的形成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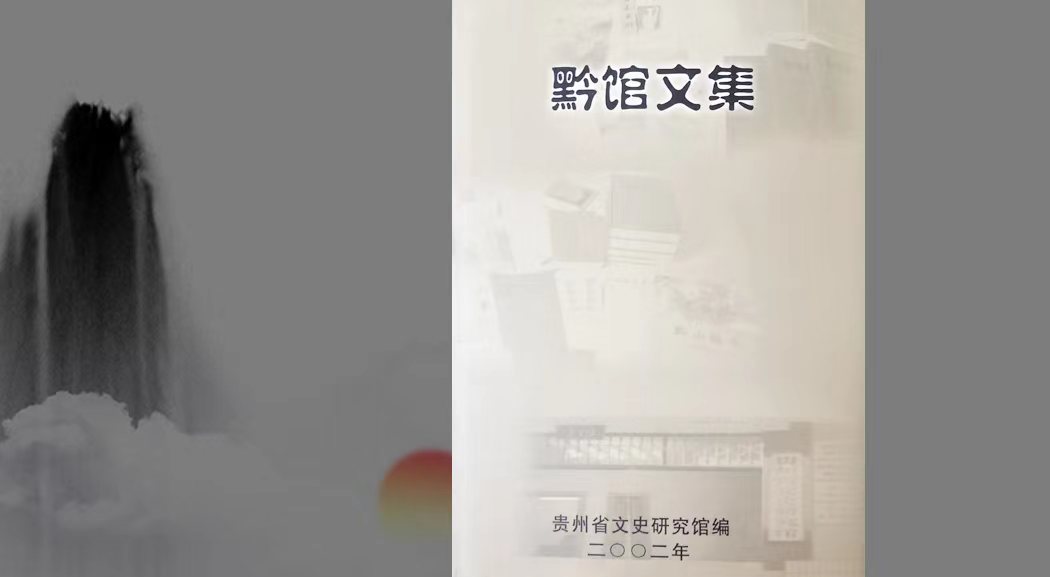
考查苗族的来源,首先应从中国史前资料进行探索。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认为:《尚书》及其他儒家著作中称:“尧、舜、禹、契(商之始祖)、弃(即后稷,周之始祖)是结合在一起的,……而对另一个氏族的有苗,则被视为是与他们各异的族系。”范文澜《汉族自秦汉起成为中国统一的国家的原因》中说:“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活动场所,原来他们也曾住在中原境内,或离开中原不远的地区。后来这些夷、戎、狄、蛮随着社会的动荡,致使各自社会的发展状况也相应地有所变化。一部分融合到华夏民族之中,一部分则分头迁徙,形成边疆山区的少数民族,演变为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还有顾颉刚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也说:“凡是春秋时的‘诸夏’以外的国家,有如楚(蛮)、秦(戎),……已经都被拉过来和向来的‘诸夏’(夏、商、周)……并作一族人了。”这个观点的提出,正与范文澜的论据同属一种类型。
现从“䜌”“有苗”“三苗”“南蛮”的含义中,试图寻出苗族来源的根据。《帝王世纪》:“帝尧陶氏,……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丹水系指今汉水上游,尧在丹水之浦作战的对方为“三苗”。而“三苗”正是“南蛮”中毗连“诸夏”的主要集团。所以,史籍对它又有“苗蛮”之称。当代语言学界提出“䜌”字曾见之于金文,认为即今通用的“蛮”字。并说,“蛮”字的古音读法与今苗瑤集团某些支系的自称相近。因而,拟定“汉语古蛮字是苗、瑶语古代自称的音译。”古代部落往往以“人”的名称作为部落的名称。在早期,“䜌”字当无贬义,后来其他强大集团把他们统治了,始在下面缀上一个“虫”字,表达是被征服的身份,从而因袭下来(见《民族语文》1983年第6期,李永燧《关于苗瑶的自称——兼说蛮》)。
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到尧、舜以及夏代的禹,已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发展到地域性的部落联盟。到夏启开始建国,甲骨文里没有国字,只屡见的中“邑”字。汤的邑有七十里,周以百里见称,他们的子孙随着武力的发展,不断扩充领土,国家的领域越来越大了。三苗集团在唐、虞、夏三代更替的岁月中逐步南移,先在汉水和淮水流域分布,随后南移到长江中游地区,据守左洞庭,右彭蠡一带地方。到春秋战国时期,它受着楚国奴隶主的残酷镇压,迫使他们有些支系向着西方和南方迁徙。三苗迁徙的分布状况,大体是西迁部分形成了苗族,南迁部分形成了瑶族或畲族。至于遗留在江汉地区的这一部分,则融合到华夏集团之中。
洞庭彭蠡之滨原是三苗集团的根据地,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被人将集团名称改为“般瓠蛮”,至此分为苗、瑶两个族,各向西方和南方山区分散迁徙。苗族中又分为两个支系:一支分布在腊尔山区,到明代朱元璋派人前来设置卫所驻兵屯垦,并筑一道边墙将苗寨封锁起来。由于屯兵奸商磕诈苗人,到清代乾嘉年间,激起苗民的大起义。同时,还有一支苗族顺着沅江而上,开辟武陵山区聚族而居。到隋、唐时期,却被外来谢氏领主进行长期统治。宋、元、明三代连续受到他族土官的奴役剥削。清代雍正王朝首先在此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置六个厅治,征税勒索白银。到咸同年间,苗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起义。
历史文献记载洞庭湖有个石矶叫“苗乌头石”,在自然物上冠以某个族名,其缘由必有所本。传说洞庭湖中的“君山”,原名“苗山”,直接与苗族名称有关。特别是,唐代两大诗人对于苗族都有具体的指点。白居易回乡过洞庭湖,有“疑是苗人顽,恃险不终役”之句。刘禹锡被贬官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写出“蛮衣斑斓布,时节礼的般瓠”的诗篇,还为苗瑶润色歌谣。以上事迹足以证实,洞庭湖原是苗瑶两族的发祥地。
此外,早在魏、晋时期,还有一支般瓠蛮即由巫峡溯江迁到巴郡境内。到南北朝战争频发年代,各族豪右聚众自雄。因而,三峡苗族也出现了封建领主,阻挠三峡水上运输,控制王朝的交通要道。这些苗族封建领主是,“蛮族大姓田氏、桓氏、梅氏、鲁氏皆信奉槃瓠,直言不讳是般瓠之后。”(见《魏书·田益宗传》)到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武帝派遣陆腾、司马裔率领大军进行镇压,致使无数的“蛮蜑”惨遭杀戮,随即四散迁徙。到公元618年,唐代统一全国,这支苗族有的仍然留在三峡两岸,有的则溯江西上,分布到渝州(今重庆市)东南地区,以及乌江下游。我国大诗人杜甫于公元766年寓居夔府(今四川奉节),发现当地有般瓠蛮分布,于是发出“五溪衣服共云山”的感叹。嗣经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派人前往川东地区普遍调查,证实川东苗族与湘西和黔东北苗族的方言和习俗完全一致。
从两江到南北朝,苗、汉交错杂居,向汉族融合的人数越来越多。唐、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时期,苗族广泛吸收汉文化,大幅度出现程度不同的汉苗融合。
作者介绍:

贺国鉴(1908-2002),字镜湖,苗族,贵州松桃人。长期以来,专门从事苗族史研究,重点调查搜集了苗族从原始社会到唐宋时期的大量史料,为参与编写《苗族简史》作了准备。《苗族简史》出版后,填补了苗族历史上没有专史的空白,并获得贵州省政府颁发的省社科成果奖。撰写苗族专题论文30多篇,参加古夜郎的调查研究工作,发表《夜郎五县故址再考释》《苗族原始社会的探讨》《陶新春传》《陶新春续传》等文。特别是对夜郎史方面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曾担任贵州省苗学会顾问,贵州史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会会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