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笔记 | 蹒跚中前行的贵州近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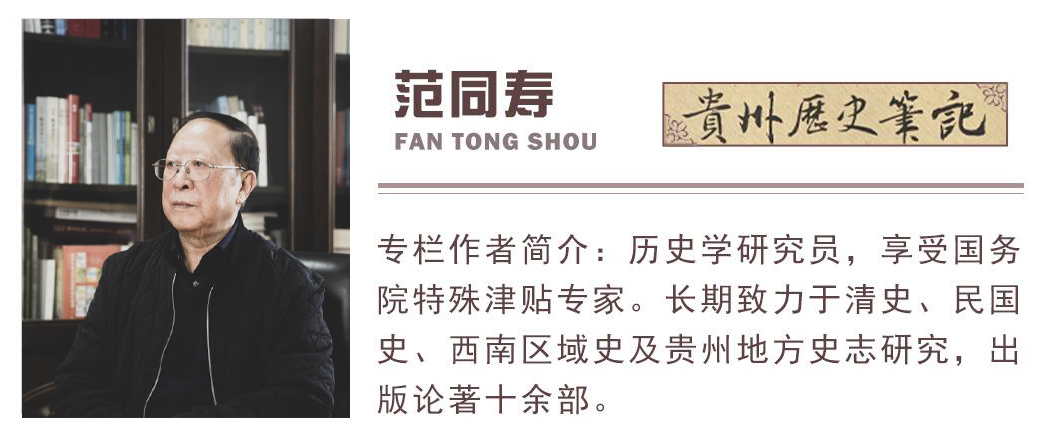

贵州近代化进程的开启,在某些方面并不比其他地区晚。但在辛亥革命后,出于各种原因,贵州陷入了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近代化步伐变得蹒跚起来,呈现出一种矛盾交织中的缓进状态。导致这种蹒跚状态出现的原因很多,主要在于全省政局的不稳定、连年无休止的战乱、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及执政者为一己私利所采取的各种怪诞政策。
就全省而言,贵州直到明清改土归流前,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封建领主制下,不少地方直到清中叶才完成从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过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严重冲击了全省尚显脆弱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本来就处于清王朝严苛压榨下的贫苦农民,为购买生活中之必需,不得不在节衣缩食的同时,改变传统种植的农产品,生产易于销售的农副产品,其中最大宗的便是鸦片与适应市场需求的各种油料作物和土特产。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的大力扶持,贵州种植鸦片的面积不断扩大,年产量多达5万余担。从鸦片种植与贩卖中抽取的“特税”,成了历届贵州军阀维系统治的经济支柱,但对于耕地面积本就严重不足的贵州农业,却成了灭顶之灾。

首先是农业生产方式与技术的停滞不前。受地形地貌的制约,贵州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分散、以家庭为单位的劳作形式。本来半封闭式的自给自足就影响先进技术的传播,军阀之间的混战更使普通民众将离家外出视为畏途,到了民国前期,不少农民仍在沿袭旧的一套耕作模式。民国初年,地处黔东南的永从县(今台江)甚至还在用人拉犁、牛踩田,用木犁犁田。肩挑背驮、传统鸡公车依然是许多地方的主要运输工具。这种生产者无力改进生产技术,世代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状况,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使广大农民长期陷入困境。一旦遇到荒年,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农户的破产便成了广大农村的普遍现象。
在贵州这个以农业为经济支柱的省份,农业的停滞与衰退,无疑使跨越近代化门坎,意欲改变贵州闭塞与落后的任何努力,都变得障碍重重。20世纪初的贵州近代化步伐其所以踉踉跄跄、步履蹒跚,显然与自身原有农业基础的薄弱,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军阀政治的为所欲为密切相关。
一位学者曾说:近代的中国是社会动乱和社会改革并举,悲剧不断与民族觉醒同生的时代(王业兴:《二十世纪初中西文化交融与中国近代化的进展》)。这一看法用在贵州的身上,似乎十分对口。尽管从1912到1935年间,贵州的政局极度不稳定,战乱、灾害几乎从未间断。但由于历史潮流的裹挟,尤其在一批进步人士的反复呼吁和力主下,无论执政者愿与不愿,摆脱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引入或创办各类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工厂,已成为时代的一种趋势。所以,即便步履维艰,诸多近代化的事物毕竟还是在贵州出现,并缓慢地向前迈出了步伐。

贵州民间有句老话戏称:生活在贵州“叫人要吼,出门靠走。”这是大山阻隔、通讯落后导致的先天困难,但也说明,要排除重重山岭的阻碍,加强与外界信息的互通,改善通讯手段是贵州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贵州邮电通信的启步早于近代交通。还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毕节至贵阳的电报线路就已架设,只不过这条线路是由外国人主持兴办的。到清末,贵阳至兴义、贵阳至湖南晃州(今新晃)、晃州至铜仁的线路都已开通,一些州、县还设有电报局。民国初年,南北两条电报干线先后架成,分别是1915年架设的贵阳经綦江至重庆的北线,以及1921年架设的贵阳经独山通往广西六寨的南线。此外,又先后架设了赤水至泸州、黄草坝至江底、镇远至锦屏等支线。加上在一些主干线路上加挂的分支线路,到1934年,全省电报线路总长已达4616.2公里,埋设电杆计4.7万根。服务于电报业务的电报局,由1912年的7个增加到1935年的33个。随着发报业务的增加,报务种类也随之不断进行变动与更改。1922年,电报只分政务、公务、特种、寻常四种;1934年,增改为政务、加急、寻常、新闻、交际、赈务6种;1935年,当局将之细化为官军、局务、私务、公益、特种等5种。
贵州电话的出现较电报晚,发展也慢。民国初年全省仅贵阳一地有电话,1926年由当时的省政府向交通部申请到一笔资金,领得总机1部和一些线材,部分机关才开始安装电话。同一时期,一些县城开始借用电报线路及架设单股铁线装接最早的城乡电话。但直到1935年,全省仍只有37个县可与邻县互通电话,而几个稍大城市安装的总机也只是5门至10门。十几年间取得这点进展,确属缓慢。
邮政虽继电报之后即已出现,利用的也是西方国家的技术设施,但直到1901年全省才有了第一个近代邮政机构。这个邮政机构设于贵阳田家巷,当时的名称为“邮界”,且只有1名工作人员。1914年,贵州被列为全国21个邮政区之一后,贵阳成立邮务管理局,下设秘书股、会计股、视察室等机构,职员增加到30人,以后几年邮政业才有了一些发展。但邮政毕竟与交通有着密切关联,交通能力不足,邮政的发展自然十分迟缓。当时,因军阀割据,战乱连年,盗匪横行,步班邮路时常中断,即使邮政种类、邮政代办点、信箱信筒之类增加虽多,业务量反而不增反减。在贵州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作为近代化代表事物之一的邮政电信业虽然陆续在贵州出现,却长期处于困窘状态。
文通书局是贵州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亮点,由1917年退出政界的华之鸿投资白银20万两所创办。该书局不仅是贵州最早使用先进印刷机器的工厂,而且堪称贵州近代企业的佼佼者。问题在于,除华之鸿的文通书局及酿酒等少数企业外,民国前期贵州工商业的发展进程几乎乏善可陈。

民国前期的贵州工商业,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虽然举步维艰,缓慢发展还是有的。这种发展在炼铁、纺织、造纸、电力、日化、兵工等行业方面有一定体现。
还在清廷决定开办青溪铁厂之前,贵州民间便已有不少土法炼铁作坊,满足农户铸造农具之需。镇远县㵲水北岸便有大小高炉、土炼铁炉若干座,年产生铁可达20余万斤。辛亥革命后,各地冶铁成风,有关文献统计,至1929年,全省冶铁业增加到31县86处51厂。其中产量最大的是瓮安土地堂铁窑,年产量达1800吨;工人最多的是龙里宋福等4家铁厂,每厂工人约300余人。虽然几乎所有的铁厂都未采用近代技术,依旧沿袭着古老的传统土法冶炼,但却解决了贵州广大农村及城市民众用铁的需求。
纺织是贵州采用近代化工艺最早的行业之一。在外国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的冲击下,传统土纱土布失去市场,各地大户纷纷投资近代纺织,加上官方所谓“劝工局”的倡导,促进了民初纺织业的勃兴。最盛时全省的纺织户多达2300家,职工总数接近8000人,仅布类一项年产就达70万匹。尽管此期间无论私营、官办的纺织企业规模都不大,但各项工序多使用机器生产,最初主要是木机,以后逐渐被铁机取代,只不过限于科技及本省的生产力水平,那时所有机器的驱动,所仰仗的都是人力。当时最大的纺织厂先是设于贵阳市南郊的兴业织布厂。该厂资本总额达5400万元,拥有织机40台,工程师2人,工人95人,年产布15吨。1927年,官府创办的省立模范工厂取代了兴业织布厂的地位,职工数达100人。加上与官办的模范缫丝厂、模范监狱工厂联成一气,所有民办合股经营或独家私营的工厂,都只能处于下风。
贵州的日化行业同样出现在20世纪初。最早的产品是肥皂和蜡烛。人们觉得肥皂比皂角方便,蜡烛比菜油灯亮,生产的人就多了起来。生产肥皂的作坊从1家发展到10家,每年生产肥皂多达10吨以上。衣裳不定要天天洗,照明则是一到晚上就要用,因此,做蜡烛的作坊也就更多。有人统计民国初期的造烛户有600余家,工人多到1400余人。不过造的多是土蜡烛,生产洋烛是往后的事。
民国前期,在近代化潮流的推动下,贵州造纸、酿酒、染织、制革、火柴、玻璃等行业也都有所发展,其中最能展示贵州近代化的,莫过于电力、兵工与交通。历代军阀出于政治、军事需要,往往会集中资金与人力开办一些与壮大军力有关的工厂。开办电厂、兵工厂,修筑近代公路便是他们的杰作。
贵州建第一座发电厂之事,笔者在本书上册《军绅政权:也不是无所作为》一文中已经谈到过。这件事虽缘起于刘显世,完成于周西成,但建成的电厂规模很小,还赶不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的一座小水轮泵站。不过,第一座电厂的修建,毕竟具有划时代意义。至于兵工企业,则是军阀们打仗所必需。上台以前周西成在赤水已经办过小型炮厂、炸药厂,当上省主席后,更是派人到上海购置各种设备,先后在赤水、贵阳扩建兵工厂,大量生产军火。早年出版的《贵州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辑》统计,位于贵阳的贵州省兵工厂,生产工人多达2000余人,规模远比占地70余亩的赤水兵工分厂大了许多。

与很多省的情况不同,贵州的近代交通并非起步于轮船、铁路。在山高谷深的贵州,要打破封闭,改变交通梗阻,最需要的是将官府修建的驿道和那些踩踏了千年以上的乡间羊肠小道,改造成可以通行马车和汽车的公路。因此,近代公路的兴建既是贵州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贵州近代化进程的首选。
1912年以后的10余年间,贵州交通状况并无大的改变。1926年后,周西成以铁腕手段在全省统一政令、整顿财政,着手修建环贵阳城的近代公路。这条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尚未竣工,这位省主席便迫不及待地想体验坐着汽车兜风的滋味,专门委人购进一辆美制雪佛兰轿车。之后,他又令贵州路政局制定出了一份《全省马路计划大纲》。其后,一条由贵阳经安顺至黄果树,真正具有近代意义与运输价值的公路于1927年底正式竣工。用当今的眼光来看,当年的这条公路确实很简陋,但它却开创了贵州交通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在跬步皆山、举步维艰的贵州,可说意义非凡。
周西成死后,贵州的公路建设仍按他所拟定的计划进行。由贵阳通往甘粑哨、毕节、惠水、桐梓、赤水、独山的公路相继动工修建。至1937年,《全省马路计划大纲》中规划的贵北、贵南、贵西、贵东4条干线公路陆续建成。贵州的交通运输,由此从单纯人力转为人力与汽车并用的时代。
据《贵州公路运输史》记载,贵州最早的公路运输只准官办。因为桐梓系首脑人物认为,“政府筑路,路权属公,汽车运输理应官办,商民不得经营”。但过了一年,官方成立的转运公司只有汽车几辆,又经营乏术,实在难以为继,只好开放商营。1934年,全省商车猛增至70辆,运营里程总长至900公里。到1935年6月,全省的公路营运几乎已全由商车承担。
僻处西南、长期处于封闭与半封闭状态的贵州,由分散、落后的农业经济跨上近代化之路,的确充满了诸多难以想像的艰辛。单就周西成将汽车分拆由水路转运到贵阳,再在贵阳重新组装这件事,当年一名考察中国公路的美国人就曾叹道:“其困难是生活在北京、上海、纽约的人所难想象的。”
贵州近代化的启动,路也坎坷,步也蹒跚,但最能吃苦耐劳的贵州人毕竟在20世纪初跨了出去。除了那些专业学者外,作为今天的普通贵州人,我们不会去考证那些历史细节,但仍需要从中感受到前人披荆斩棘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