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帛书的起源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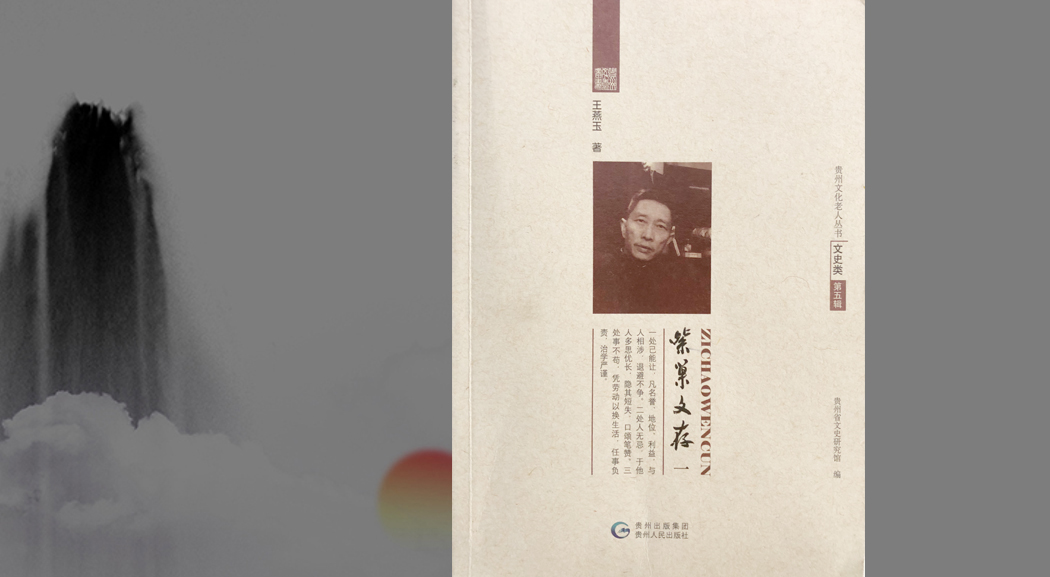
一处己能让,凡名誉、地位、利益,与人相涉,退避不争。二处人无忌,于他人多思优长,隐其短失,口颂笔赞。三处事不苟,凭劳动以换生活,任事负责,治学严谨。
——王燕玉
帛书的产生已无法确指,按理推断当较晚于简牍,大概春秋简牍行时,并用丝织品写文章。《论语》记孔子弟子子张写字于衣带,侧面可证。其故不难理解,自因简牍笨重累赘断烂,不易清理,而丝织品宽薄柔软,抒卷裕如,用来写书轻便,遂与简牍同行。无奈价格昂贵,书的分量若大,少数人用得起,大多数人却无力购备。所以,写书主要地位还让简牍占领。
缣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殷商、西周丝织品应用尚狭,春秋、战国品种渐广,丝织品总称帛,又称缯。单丝所织白色的,称素;生丝所织白色的,称绢;熟丝所织白色的,称练;双丝织微黄的,称缣。从而,丝织写的书通称帛书或缯书,分称素书、绢书、练书、缣书。而写者最喜用细密柔韧的缣,于是以“缣帛”为写书代词。
缣帛写书本身灵活,可依文章篇幅长短而定,一篇文章写完剪裁下来,折叠存放。晋张揖《字诂》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谓之幡纸。”这是不长不短者的合度办法,任何缣帛仍有限度,非能无限接长,或者无限截短,故简策的篇、卷状况,仍移适于缣帛。短文可数篇合一卷,长文可一篇分数卷,通常是一卷相当简策的一篇。一卷左端粘轴,由左向右裹收,右端起首一段缣帛,空着不写以作保护,也叫襟。首和身用的料多取两色,卷子便形成帛书的基本形式,但非唯一形式,还有上面说过的折叠形。
帛书始终未能普及,却也由少趋多进展。西汉刘向校书竹、素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用缣帛,而厌用简策。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胁迫迁都,从洛阳徙长安,将卒大毁宫廷藏书,以简策来烧火,以帛书联缀作帐篷、车篷、口袋,可想帛书数量非小。
帛书初行阶段,即用做衣缣帛,后为渐趋讲究,专门织造供写书的缣帛,上面或画织界阑,红色的叫朱丝阑,黑色的叫乌丝阑。东汉顺帝时,襄楷得于吉的《太平青领书》,共一百七十卷,艳称“素书朱介青首朱目”。说的就是白素上画红色界阑,青绫作首,文里分段小标题字以朱墨写,衬着乌黑的字,何等灿烂夺目。
汉末已较普遍用纸,而贵族文人间习于贱纸贵素。如崔瑗以纸抄写《许子》十卷赠友人葛元甫,特附一信致歉,说贫居买不起素,只得用纸了(见《北堂书钞》引)。大书法家蔡邕自矜其字,若非纨素不肯下笔。以至三国,魏文帝曹丕将自著《典论》用素写赠孙权,用纸写赠张昭,既示君臣之差,又表尊孙之意(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
综观缣帛写书,产量少,价钱高,成为文房奢品,是其甚大局限。前阶段与简同使,后阶段与纸并用,到底无法代替二者,不能辟为独立范畴。人们追求一种具缣帛的优点,而无其缺憾的写书形材,便发明运用纸。
帛书实物
1965年,于长沙楚墓发现帛书,可惜都是碎片,失去原状,无从辨认其上文字。因丝织品入土易腐,历久不保。惟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是用生丝平纹织成,细密均匀未烂。整幅者高约四十八厘米,半幅者高约二十四厘米,横摊竖写,有的用朱砂画上下横阑,每两行字间亦用朱砂画直线,即上述朱丝阑规格;有的非朱丝阑,字也写得随便;有的一种书已写毕,却未剪断,由左边另一行又开始写另一种书,这另一行前面画一个黑小方块,作为区别标志。有的卷在竹木条上,有的折叠置漆盒内,可见两种方法西汉初同用。这批帛书整理算计,共二十多种,约十二万字,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书、哲学、历史著述居多。其中,史书竟有司马迁未见的,如《纵横家书》为汉初所写,二十七章,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史记》,文字略同,另十六章则早失传,保存着苏秦的书信、谈话,学术价值倍见珍贵。这批帛书多而完整,真可谓空前大发现。

王燕玉(1923-2000年),贵州遵义县人。1949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遵义豫章中学、遵义第四中学、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1973年调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历史文选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81年评为副教授,1988评为教授。王燕玉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贵州古、近代史,贵州方志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古籍文献等领域,出版了《贵州史专题考》《中国文献综说》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专题文章。参与编撰《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