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今日立春,春已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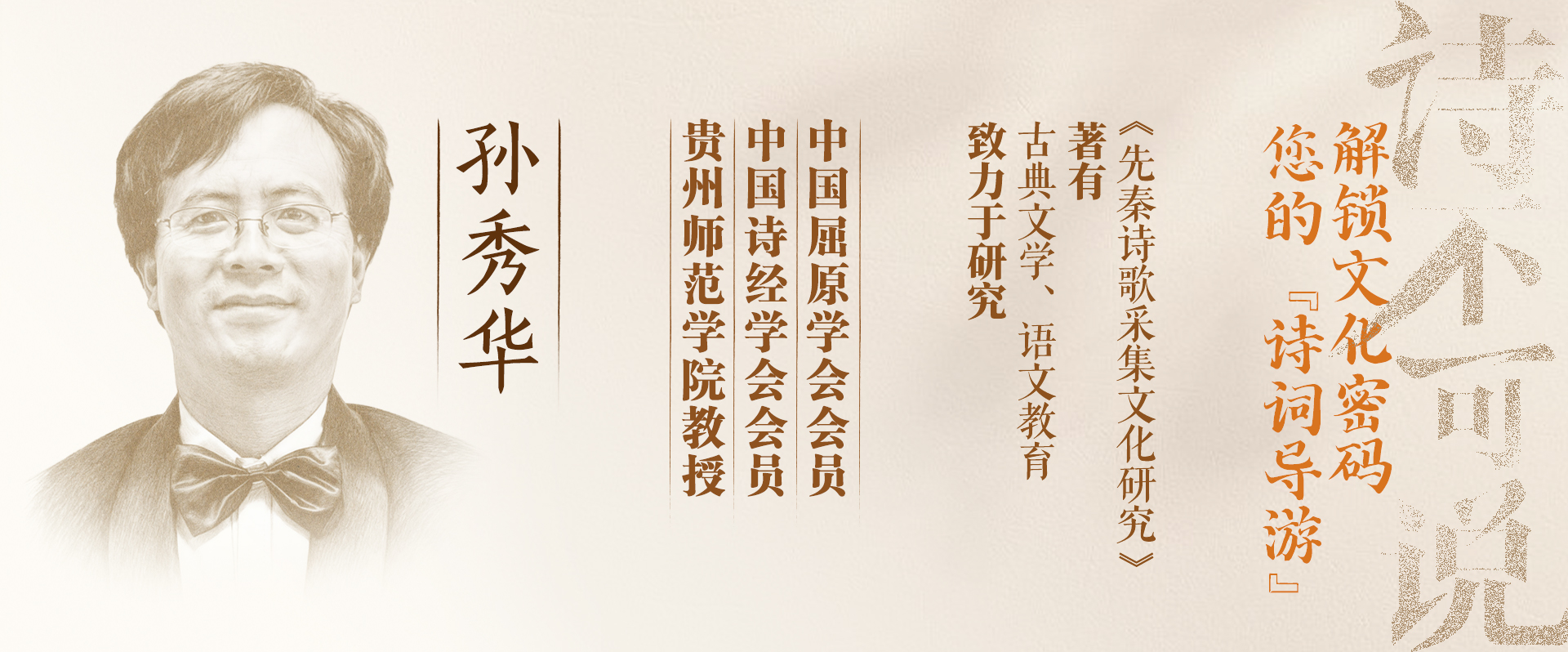
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腊月二十二立春,辛弃疾填词《汉宫春·立春》有云:“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而他所注视的不仅是发簪上颤动的立春彩胜,更是一个文明对时序更迭的集体仪式。那些精巧的绢花,是冬的休止符,也是春天业已开启的书写于美人发髻上的宣言书。
今年的立春节气,正在今天,腊月十七。今日立春,春已归来。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杜甫流寓夔州(今重庆奉节)。又是一个立春日,面对眼前的春盘,他的思绪却飞越关山,回到“两京”长安与洛阳的春梅绽放的美好时节。杜甫《立春》诗曰:
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
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
巫峡寒江那对眼,杜陵远客不胜悲。
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

诗句平静无奇的叙述下,暗涌着惊心动魄的史实与萦绕不去的乡愁。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大唐的春天再也回不去了,两京立春的繁华只有在忠臣的梦中追忆。春盘本为迎新习俗,却成了怀旧的媒介。“生菜”的青翠反而刺痛了杜甫,那故乡洛阳杜陵家中窗外的寒梅花,怕是又开了吧,只是原先的赏花人现已散落天涯。
杜甫的敏锐在于,他能从最日常的节俗中,打捞起一个时代的重量。当他轻轻说出“此身未知归定处,呼儿觅纸一题诗”时,那书写于纸上的笔墨也便成为了他个人、家庭以及一个时代在动荡中漂泊的见证。此情此景,“立春”于他,不是万象更新,而是“旧日”的幽灵在“新生”的仪式中显形。春盘越是精致,越反衬出世事的荒芜;节物越是新鲜,越提醒他年华的老去。
这种“以乐景写哀”的笔法,成了后世处理集体创伤的模板。书页翻到唐末,韦庄在《立春日作》中冷冷写道:“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皇帝的逃亡与柳树的发芽形成残酷对照。春色依旧,只是看似山河行将易主。柳的“无情”,实则是历史的有情——它记住了所有辜负与被辜负的人。杜甫式的悲悯,在此淬炼成一种尖锐的讽喻。

苏轼的立春诗词多达十余首,几乎可以看作是他的半部个人编年史。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立春节气,苏轼正在密州任上,于病中写下两首七律。其一有云:“孤灯照影夜漫漫,拈得花枝不忍看。白发攲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画面透着孤寂:灯影、病躯、白发、药粥。按说这是典型的“衰年立春”题材,但这是“欲扬先抑”,接下来苏轼笔锋一转写到:“东方烹狗阳初动,南陌争牛卧作团。老子从来兴不浅,向隅谁有满堂欢。”民间立春的喧闹节俗闯了进来,与他“向隅”的冷清形成喜剧性反差,彰显了苏轼在困顿中自寻光亮的超迈旷达。
苏轼《元祐九年立春》诗曰:
熊白来山北,猪红削剑南。
春盘得青韭,腊酒寄黄柑。
诗里苏轼炫耀才学,二十字的小诗之内集齐了白、红、青、黄四种明艳的色彩,还另加北、南两个方位词,且每一句诗都说了至少一种美味的立春节令食物。而所谓“熊白”,是指熊背上的脂肪,古人认为色白如玉,味甚美。
对于这首诗,苏轼自己特别喜爱,甚至稍加改动,自我复制到了另一首立春诗里。苏轼《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诗里对应这首《元祐九年立春》诗的内容,几乎一致,苏轼的诗句是:“白啖本河朔,红消真剑南。辛盘得青韭,腊酒是黄柑。”看来这两首诗或者本就作于一时。与朋友在一起立春雅集,喝着“腊酒”吃“春盘”,苏轼的表达里,咬下一口青韭,就是咬住了整个春天。
写此《元祐九年立春》诗时,苏轼在定州知州任上。苏轼于前一年十月“受命出帅定武”,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衔出知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而写此诗后大约四个月,至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四月,宋哲宗行“绍述”之政,恢复神宗“新法”,宣布改元“绍圣”,该年号名称取自“绍述先圣”的政治理念。因此,这“元祐九年”,其实也是“绍圣元年”。宋哲宗改元“绍圣”后,苏轼被取消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称号,罢定州知州,以左朝奉郎(正六品上散官)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成为元祐大臣中第一个被褫官、夺职、降阶远谪僻远小州者。

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立春,陆游在夔州填词《玉楼春·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身如西瀼渡头云,愁抵瞿塘关上草。
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幡判醉倒。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上阕是典型的放臣口吻,流落、破衣、尘满面。可下阕突然扬起声调,既然春盘年年好,何不戴银幡、醉一场?但醉眼朦胧中,他看见的是“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这句看似旷达的自宽之词,反而流露出他内心深处的忧虑,他怕的不是在春光中老去,而是在年华老去中一事无成。
时间成了陆游与自我谈判的筹码,二十年后,宋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立春日,陆游《立春》诗云:
绍熙又见四番春,春日春盘节物新。
独酌三杯愁对影,例添一岁老催人。
菊芽冒土如争出,柳色摇村已渐匀。
身是兰亭山下客,未容逸少擅清真。

他细数着“绍熙又见四番春”,感慨“独酌三杯愁对影,例添一岁老催人”。但奇妙的是,陆游的愁绪很快被自然生机化解,他感叹“菊芽冒土如争出,柳色摇村已渐匀”。个人的衰老与万物的新生之间,他找到了某种平衡——生命会老去,但生命之力永远在“冒土”“争出”;同样作为“会稽山阴兰亭”的文化人,已年近七旬的陆游要与那东晋名士王羲之王逸少争一争谁更“清真”。
如果我们把目光从诗人身上移开,聚焦于他们反复书写的物象如春盘、春幡、春胜、春牛、春饼等等,也便会发现,这些特定的节气风物与节气物候一道构成了立春的“物质诗学”。如杜甫、苏轼、陆游都写到了春盘。一盘之中,有青韭的辛辣鲜香、或也定有萝卜的爽口甘脆。而春盘不仅是食物,更是色彩与味道的哲学,青属木,对应春天;辛味发散,呼应阳气升腾。而当苏轼笑叹“白发攲簪羞彩胜”,陆游“试戴银幡判醉倒”,他们是在不自觉的进行着一种关乎节气的神圣的身体仪式,通过佩戴特定物品而获得与天地神灵的沟通交流,以获得赐福佑护,平安顺遂。
今天,日历软件自动推送“今日立春”,直播带货、网店、超市使苏轼傲娇写进诗里的青韭、黄柑等完全不再具有季节稀缺性。而我们重读这些名家的立春诗词,仍有助于我们清晰地感知冰面的纹理、东风的湿度、泥土的松动……在残冬中辨认初春,在绝望中孵育希望。而这,或许就是所有立春诗词最终想告诉我们的终极秘密,春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勇敢美好的心灵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