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笔记丨抗战时期短暂繁荣的贵州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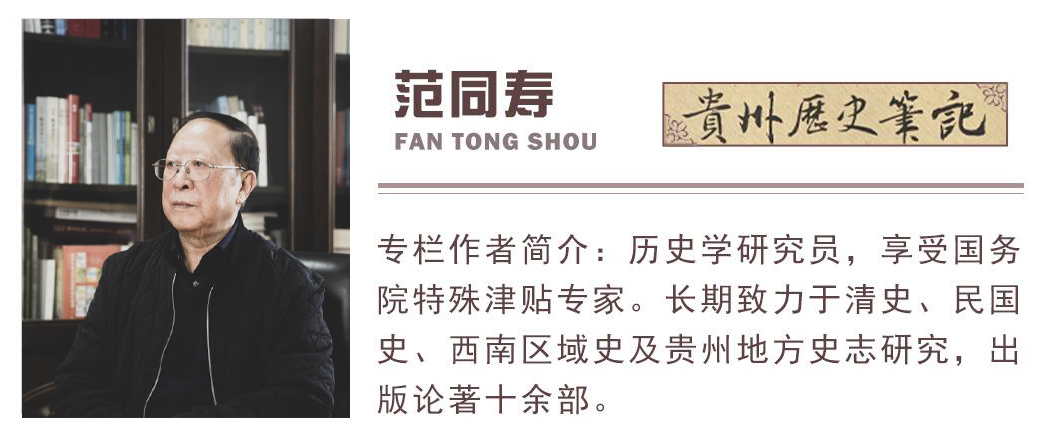

贵州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几次发展机遇,但贵州都没有抓住,其中,抗战期间的这一次最为典型。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高校、企业的内迁,科技、人才,甚至资金大量涌入,昔日闭塞落后的贵州,一下成为抗战的大后方,成了大批优质高等院校、近代军工与民用企业、各种先进科学技术人才,以及积聚了大量财富的绅商们的归宿地。这股内迁潮,给同内地和沿海发达地区有着极大差距的贵州,带来了本需数十年才能出现和拥有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商贸市场和资金,贵州的社会生产力因之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短短几年中,全省的工业、农业、交通、商贸、教育文化都发生了巨变,呈现出一种突发性繁荣。
用“繁荣”这个词来形容抗战时期的贵州,一点也不为过。
客观地说,从清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贵州社会的确在发生着变化。从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企业——青溪铁厂的兴办到民族资本家创办的文通书局跻身国内七大书局之列,从各类小型作坊式生产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地面到建设省内、省际公路及开办汽车运输业务,都显示出社会在演变。然而,历时半个世纪,贵州社会的基本面却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全省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各省中仍居于末尾。正如张肖梅先生在《贵州经济》一书中所言:“黔省地处云贵高原,有‘山国’之称。由于交通闭塞,社会经济停滞于农业经济状态。”
作为贵州经济主体的农业,虽在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经历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农村家庭手工业与农业逐渐分离、商品化的农副业生产比重有所增加等变化,但这些变化在交通梗阻、地区之间差距悬殊的贵州,仅局限在城镇周边及与之毗邻地区。就全省范围而论,绝大多数农民,尤其那些世代生活在僻远山区的群众,依然固守着世代沿袭的“刀耕火种”“ 轮歇丢荒 ”的耕作方式,广种薄收,过着勉强能够果腹与御寒的贫苦生活。对他们这些贫困者来说,世界并没有什么改变。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前线战事的激化,作为大后方的贵州既要向前线提供军粮,又须面对西迁潮中入黔高校、工厂、机关团体的粮食需求,还得解决成千上万难民的吃饭问题。面对所有一切,当局都只有向农民索取,公买公卖,高价收购自然不可能,强征硬夺倒是家常便饭。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本就难求一饱的农民,只能挣扎在死亡线上,何谈改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
工商业的情况较之农业也好不到哪里。虽然20世纪初贵州即有了文通书局这样的近代企业,但仅为凤毛麟角。一些资料统计,1911年时全省即有工厂120家,涵盖织造、机械、日化、印刷、食品加工等领域。表面上看发展势头不错,实则这一数字是按清末农商部“凡一户之制造品,有七人以上工作者,均得称工厂”的标准统计出来的。不说其中大多属手工作坊,只有四五个人的作坊还占了大多数。即便是全省唯一的发电厂,所发之电专供省政府照明尚显不足。至于 20至30年代修建的公路,因全省经济力量薄弱,从1930年10月准许商民从事运输,颁布《管理民办车运条例》,到1935年,全省仍只有车行52家、汽车75辆,资本总额不过35.4万元。商贸方面,从省境外输入的一直是以洋纱、洋布为主的舶来品,输出的大多是本省的矿产品与农副产品。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则只能从城镇周边形成的集市及省城一带的商贸市场中去感受。
抗战期间的大后方地位,给贵州带来了加快近代化步伐、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良机。短短几年间,从农业到工业、从军工到民用、从教育到交通、从分散集市到到商品集散地,整个贵州的面貌发生了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城乡经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抗战进行到1938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同年2月,日本侵略者企图调华北方面军南下和华中派遣军会合,与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展开会战。鉴于当时的抗战形势,国民政府为稳固后方基地,以解决抗战所需之军粮、副食及物资,决定采取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并在资金、技术方面加大投入。这才是贵州农业改进所成立的历史背景,绝非某位甫获委任,屁股尚未坐热的“省座某公”心血来潮所能办到的。
贵州农业改进所所长系原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林学家皮作琼,所内设置的八个系分别为:农艺、森林、畜牧兽医、柞蚕、农业经济、植物病害、经济昆虫、农业工程。除设在油榨街原省立林场的本部外,农改所还设有施秉美棉繁殖场、遵义柞蚕试验地,以及省直辖联合农场、血清制造厂、马车制造厂、农艺实验场等。贵州农改所从成立到抗战胜利,的确在推动全省农村与农业经济发展上做了不少工作,尤其在研究与改进贵州农业技术、森林保护、发展蚕牧、推广兽医,在改良农作物品种、优选苗木、加强防疫,以及培养训导省内农业技术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可观成效。这对改变长期封闭于崇山峻岭中、世代恪守传统耕作方法的贵州农业,无疑会产生一定冲击。尤其在交通便利、与城镇相近的地区,劳动者得到的帮助最多,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与生产力的提高显而易见。
不可否认,抗战时期贵州的农业的确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化。典型的表现为:改良和引进了一批水稻、棉花、大豆、马铃薯等良种,推广了各种蔬菜、花卉、绿肥作物;贵州森林植物得到了普查,进行了大批经济林木的移植试验,扩大了林木种植;推广了家畜杂交繁殖与疾病防治;进行了农具改良,蚕桑、茶叶种植研究,烤烟引进与大面积推广;成立了贵州农学院,省立贵阳高等农业职业学校,以及省立江口、锦屏、湄潭等农林职业学校、农业教育机构。此外,农田水利、战马养殖、农副产品生产等方面,在这一时期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农业的这种进步,属于抗战期间贵州经济繁荣的一个方面。

工业的蓬勃发展在战时贵州表现得十分抢眼。除了直接生产武器的军工企业外,电力、机械、化学、卷烟、纺织、造纸、印刷等行业似乎一下跨上了几个台阶。生产设备之先进、技术工艺之新颖、产量与质量之提升都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周西成办的发电厂,不过是让省城贵阳的老百姓开了眼界,见识到了什么是电灯。经过抗战期间的发展,随着投资的扩大、设备的增加,仅贵阳电厂的发电量便达到了1040千瓦,6年间增长了36.6倍。工业用电量亦从20.2千瓦,增加至832.7千瓦,增长了41.2倍。发电量增加的关键还在于,原全省仅贵阳有一台发电机,到抗战期间,遵义、安顺、铜仁、兴义、贵筑、惠水、息烽、镇远、贵定、清镇、马场坪都办起了火力发电厂。尽管各地电厂所发的电,还不能让老百姓都享受到电灯照明,却反映出贵州电力工业在缓慢进步。
民用机械的快速发展推动了贵州近代化的步伐。继1938年省政府主办模范工厂,生产汽车零件、日用消费品、医疗器械之后,省城与各地陆续建立起来一批民用机械企业。其中,新生五金厂、中国煤气机械厂、贵阳汽车修理厂、贵阳民生工厂、贵阳瑞丰机器厂、贵阳义兴机器翻砂厂等规模都比较大。到1943年,全省具有一定规模的机械厂达32家,这还不包含性质相近的店铺与作坊。如果把从省外迁入的各类军工企业也计算在内,贵州的机械制造业在战时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则更加可观。
化学工业既属民用,又与军事关系密切。贵州战时的化工企业主要生产炸药、肥皂、蜡烛、酸碱、橡胶、酒精等。炸药生产无疑有助于开山筑路、采矿加工,但橡胶与酒精在战时则是重要战略物资。贵州的区位使之成为抗战大后方运输枢纽,来往汽车络绎不绝。战争的蔓延导致东南亚橡胶供应中断,长途奔驰的汽车却不断需要更换车胎,贵州橡胶厂的建立有效满足了这一需求。先是1940年中南橡胶厂在贵阳设立分厂,之后,建业、科达、永生等厂陆续建立。这些橡胶厂翻造汽车车胎,生产刹车皮碗、汽车电瓶硬壳等产品,解决了交通运输之急需。
酒精在战时可作替代品弥补汽油供应之不足。抗战中期,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发展酒精生产。到1943年,贵州核准登记的酒精厂发展到52家,分布于贵阳、各较大县及地处交通要冲之城镇。其中,遵义酒精厂、中国植物油料厂贵阳分厂、贵阳三一化工厂、遵义兴华酒精厂、贵阳四民酒精厂、贵阳源源酒精厂,每年酒精的产量都在10000加仑以上。
其他如卷烟、水泥、棉纺织、造纸、印刷等行业,在抗战期间都获得了快速发展,不仅规模扩大、厂家增多、产量提高,而且购销两旺。这些行业产品,对于支持前方的抗战,解决本省民需都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矿冶业在战时的兴旺与发展,也给未来贵州的资源开发奠定了一定基础。

1937至1945年间,贵州商贸发展之快超出任何人的想象。《贵州省志·商业志》记述了当时的情况:1937年,贵阳市工商业仅为1420户,到1945年,猛增至5422户。具体到专属商贸的店家,除经营印刷、橡胶、皮革、服装、卷烟、肥皂、机器配件的商户外,陆续从省外迁来的有纱布百货店16家、餐馆16家、汽车材料81家、汽车运输21家、五金7家、图书文具26家、杂业291家。如果加上本省人开办的店铺,总量还不止此数。
对于当时仅有20余万人的贵阳来说,一下冒出如此多的商铺,其繁华程度,不亚于已在日军铁蹄下的内地与沿海城市。据有关资料统计,1937年贵阳工商业的资本总额仅为180万元,1943年猛增至1.06亿元,到1945年更达到2.1亿元,8年中商业资本扩张了116倍。据《贵阳市工商业调查录》记载,在贵阳商业中,大型商店集中在百货、绸缎、药品药材、饭店、钟表等行业。内迁的西门子钟表公司还在大十字修建起一座钟亭,四个钟面朝着东、西、南、北,下有警察指挥交通的站台,上刻有西门子公司店名。当时,贵阳市商铺中,最多的是旅馆,达415家;其次是茶楼酒肆,达219家。这与当年因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迁入有着明显关系。
除了省城,全省各地的商业同样走向兴旺。不仅安顺、遵义等中型城市呈现出商品增加与资本扩大,出现了商业的专营化与行业结构演变,有了新型大百货公司,即便一些边远县份如贞丰等地,也都展现出不同程度的商业兴盛。1942年,贞丰县的经商人数竟达到4000余人,其中的者相、龙场两个镇,分别有813人、325人。全县经营盐业的商贩多达百余家,少时也有数十家。这种商业的突发性繁荣,既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
上述种种,给贵州经济带来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的近代化、商业的兴旺、金融业的扩张、城镇的扩大与人口的骤增,加上战时交通、邮电通信等硬件建设,整个贵州在这段时间,的确展现出一种经济上超乎想象的繁荣。遗憾的是,这种突然降临的繁荣,是仰赖于抗战时期独特的大后方区位优势形成的战略优势,加上大批内地与沿海的工矿企业、教育机构、富商巨贾与大量难民涌入带来的结果。待到抗战胜利,全国局势发生变化,情况迅速发生逆转。

对于贵州这场潮涨潮落般的经历,学术界论者甚众,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片面的观点也不少。其实这一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虽只给贵州带来了经济上的短暂繁荣,却也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贵州山区经济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过于强调这场突发性繁荣的战时性、脆弱性与被动性,过于强调战时所处大环境的作用,只看到战后经济的迅速衰退,那就很难对贵州历史进程中的这番经历,做出客观准确的评价。
我们研究既往的史事,讲究的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贵州发展的滞后是由各种综合因素导致的,区位、地质地貌、交通、极少的可耕地等,长期制约着贵州的经济发展及与外界的交流。在单纯农业经济时代,无论贵州人如何世代拼搏,都不可能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赶上有着肥田沃土的中原与江南。但自近代以来,生活在贵州的各族群众一直在竭尽努力,在近代化道路上缓慢而执着地行进。近代钢铁厂的率先兴办、公路的兴修与运输的改变、邮政试办与电信线路的架设、各类学校的创办,等等,都代表着这片落后山区已开始向近代化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