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小暑诗话,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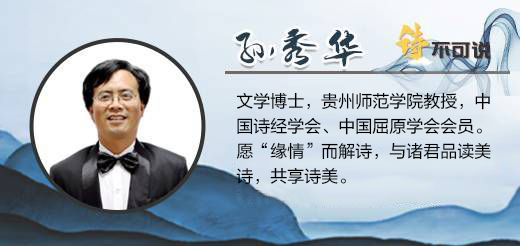
时序匆匆,忽已是小暑时节,7月7日04时小暑交节。
小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一个节气,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标志着季夏时节的开始,即《诗经·小雅·四月》所云“六月徂暑”之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曰:“暑,热也,从日者声。”“暑”表示炎热的意思,“小暑”是指天气已经开始变得炎热,但还没有达到最热的程度。而中国人的智慧又很是讲究对称,既有小暑,则有大暑,“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以及大暑洋溢着夏天的火热,而这两个节气又与冬季表示寒冷的小寒、大寒两个节气正好遥遥相对。
 来源:新华社
来源:新华社
关于小暑节气的物候,《逸周书·时训》有曰:“小暑之日,温风至。”意思是说,小暑到来,温热之风已无以复加,达到极致,清凉不再,热浪滚滚。而小暑三候是:“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鹰始鸷。”其中“蟋蟀居宇”的说法可追溯到《诗经》,《诗经·豳风·七月》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宇”是指屋檐,“八月在宇”意思是说,小暑时节,蟋蟀已来到屋檐之下。而三候“鹰始鸷”,则据《礼记·月令》之“(季夏之月)鹰乃学习”记载,是指可以见到今年的新生一代的鹰开始进行猎杀。“习”字本写为“習”,《说文解字》释曰:“習,数飞也。从羽从白。”故而从本义上讲,“鹰乃学习”是指新鹰练飞,而由“鹰乃学习”衍生出的“鹰始鸷”,则是指新鹰开始猎杀小鸟、兔、鼠、蛙、蛇等小动物。
最早直接写明小暑节气的诗歌,来自南北朝时期。北周庾信《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其二十二》诗曰:
百川乃宗巨海,众星是仰北辰。
九州攸同禹迹,四海合德尧臣。
朝阳栖于鸣凤,灵畤牧于般麟。
云玉叶而五色,月金波而两轮。
凉风迎时北狩,小暑戒节南巡。
山无藏于紫玉,地不爱于黄银。
虽南征而北怨,实西略而东宾。
既永清于四海,终有庆于一人。
这首诗出自一组大型歌功颂德礼乐歌诗。诗中“凉风迎时北狩,小暑戒节南巡”两句,是说皇帝按照时节出巡,应秋季之侯向北方巡狩,在夏天到来则向南方出巡。“戒节”一词,即“告知节候,谓当令”之意,是在告诫天下人,节令已到,要按“时”劳作。而历史上的“戒节”,也有直接出自皇帝诏书的明确记载。比如,《后汉书·明帝纪》载曰:“十二月甲寅,诏曰:‘方春戒节,人以耕桑,其敕有司务顺时气,使无烦扰。’”如此看来,则在中国古代关于节气物候的“宣示”也明确纳入了“天授皇权”的范畴,而后世所谓的“劝课农桑”,其实质当然也就是这种权利的执行。
 来源:新华社
来源:新华社
“阴阳争而催小暑。”时序变迁,“小暑”也被写进诗篇里,抒发思念之情与离别叹惋。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韩翃《赠别王侍御赴上都》诗有云:“幸有心期当小暑,葛衣纱帽望回车。”又如,中唐武元衡《夏日对雨寄朱放拾遗》诗曰:“才非谷永传,无意谒王侯。小暑金将伏,微凉麦正秋。远山欹枕见,暮雨闭门愁。更忆东林寺,诗家第一流。”武元衡又有《送魏正则擢第归江陵》诗云:“客路商山外,离筵小暑前。高文常独步,折桂及龆年。关国通秦限,波涛隔汉川。叨同会府选,分手倍依然。”但仔细研读这韩翃、武元衡的这三首诗,其实很难确指诗中所说的“小暑”是指小暑节气,但却又总归可以指向“小暑时节”。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而中唐时期敦煌文献《咏廿四气诗》中的“小暑”诗篇则是非常明确的。《咏廿四气诗·咏小暑六月节》诗曰: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
竹喧先觉雨,山暗已闻雷。
户牖深青霭,阶庭长绿苔。
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催。
诗歌中小暑三候都点出来了,第一句有“温风至”正是小暑一候,第七句“鹰鹯新习学”对应小暑三候“鹰始鸷”,第八句“蟋蟀莫相催”暗含小暑二候“蟋蟀居宇”。而中间四句也很有才情,三四句写雷雨时有发生,以翠竹、青山为底衬,却又诉诸听觉;五六句从视觉入手,写深夏庭院绿荫清凉,台阶上也长满了绿色的苔藓……如此季夏风景,自是声情如画。
 来源:新华社
来源:新华社
而小暑时节“鹰鹯新习学”,也可以说是大唐文士的共识。比如,“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登沃州山》诗有曰:“小暑开鹏翼,新蓂长鹭涛。”其中的“小暑开鹏翼”,也正是在说,小暑时节,新生的大鹏鸟要张开翅膀练习飞翔。
宋末元初方回《夜望》诗云:
夕阳已下月初生,小暑才交雨渐晴。
南北斗杓双向直,乾坤卦位八方明。
古人已往言犹在,末俗何为路未平?
似觉草虫亦多事,为予凄楚和吟声。
这首诗很是难得,至少表面上是写出了小暑时节的“夜观天象”。颔联说:“南北斗杓双向直,乾坤卦位八方明。”这比较清晰地指明,小暑时节之晴夜,可见壮美的夏季银河从东北地平线向南方地平线延伸,北斗七星与南斗六星恰遥遥相对,于此际则天地乾坤各居其位,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向明确无误。当然,深究下去,则情况可能会复杂得多。
方回(公元1227—1307年),字万里,一字渊甫,号虚谷,别号紫阳山人,歙县(今属安徽)人。宋理宗景定三年(公元1262年)进士,调随州教授,历江淮都大司干官、沿江制干,迁通判安吉州。初媚贾似道,时贾似道鲁港兵败,又上十可斩之疏。召为太常簿,以劾王爚不可为相,出知建德府(属两浙西路,治建德县,辖建德、寿昌、桐庐、分水、淳安、遂安6县)。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元兵至建德,以城降元,改授建德路总管兼府尹。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赴燕觐见,归后仍旧任。前后在郡七年,为婿及门生所讦,罢,不再仕。以诗游食元朝新贵间二十余年,也与宋遗民往还,长期寓居钱塘。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卒,年八十一。
 来源:新华社
来源:新华社
方回文名显著,其《千顷堂书目》及《瀛奎律髓》尤为成就非凡。纵观其人生履历,正可谓多事之秋,而其“以宋守土官腼颜仕元”,多为士林不齿。明白了这样的背景,则看似简简单单的“南北斗杓双向直,乾坤卦位八方明”一联诗,显见又或即方回为赞美新朝而发出的“雅正”之“心声”。但人的情感毕竟又是最复杂的,尽管身列元朝新贵,但他终归还是大宋遗老,我们也就不能武断地认为方回接下来诗句中的“凄楚”之情是无病呻吟,是矫情虚伪。
更为明确写于“小暑日”的诗篇也有,如,南宋刘克庄《小暑日寄山甫二首》。又如,明代黄省曾《小暑日张月鹿何叔皮至馆》:
朱光下檐隙,绿影荡帘间。
鱼沼平翻藻,龙城曲抱山。
升霞久延伫,挹翠共乘閒。
新霁从曛黑,天河照马还。
“佳者熟当小暑时”,小暑时节,新鲜荔枝上市,也多有见诸歌咏。明末清初林古度《荔支词十首·其六》诗曰:
乡风交送满堂前,时候初当小暑天。
中贯金钟名色异,高肩细核妙如仙。
这是一首“白战体”诗歌,句句写荔枝,句句不明说荔枝。但荔枝初上市,“时候初当小暑天”是确定无疑的。清初查慎行写有诗歌《汪悔斋方伯署庭有荔支,小暑后摘以见饷,率成十六韵》,而查慎行《题酉君画荔支图二首·其一》诗云:
四月则太早,七月则太迟。
上品贵适中,熟当小暑时。
其株皆合抱,赪实高累累。
色香与味三,妙取带叶枝。
金盘荐华屋,不以远见遗。
向非玉堂仙,谁写冰雪肌。
冰雪故难剖,略烦点胭脂。
如披蔡家谱,而读苏公诗。
这是一首题画诗,应是直接写在画卷上的。前四句写荔枝成熟的季节,“熟当小暑时”——四月太早,七月太迟,正当其时,则是五月底六月初,恰是小暑时节。
而关于小暑三候之一候“温风至”,也有“热风达到最高程度的至极点”之理解。乾隆《月令七十二候诗·其三十一·六月小暑节三候·温风至》诗曰:
南风曰巨即温风,至极至来训不同。
季也定非来以始,夏哉应是极而终。
登台拂拂面犹扑,挥扇炎炎汗更融。
却忆良农方炙背,三耘努力卤田中。
对于“温风至”的“至”字,乾隆皇帝特意注解说:“至,亦训极,亦训来。季夏暑气之至极,故曰‘温风至’,非谓其初来也。”意思是指,季夏天气,暑热之气达到了极点,因此,这个“温风至”不是说“温风初来”。小暑时节,正处“热在三伏”,乾隆皇帝的这一解说应该是很正确的。
 来源:新华社
来源:新华社
“喜闻知了声,尚畏小暑雷。”小暑时节,蝉声悠扬。清代乔远炳《夏日》所写蝉声里的“小暑”,清凉悠闲,自在逍遥。乔远炳《夏日》诗云:
薰风愠解引新凉,小暑神清夏日长。
断续蝉声传远树,呢喃燕语倚雕梁。
眠摊薤簟千纹滑,座接花茵一院香。
雪藕冰桃情自适,无烦珍重碧筒尝。
晚清李慈铭则有诗专写“小暑闻蝉”,写蝉翩然飞来,蝉鸣幽幽,“为我清心颜”,仿佛“知我心者”。李慈铭《小暑闻蝉》诗曰:
玉衡指在未,城居始闻蝉。
赁此半亩地,绿阴亦便娟。
翩然不我弃,冠緌来周旋。
肯惜数声啭,为我清心颜。
径芜绝车马,家贫无管弦。
午风作幽弄,顿觉烦热蠲。
祗恐轻翼驶,顷刻邻乔迁。
须知此中树,所灌皆清泉。
下有曳杖翁,自辟山林天。
盍来伴啸咏,月照虚堂眠。
而再往南方数说,则小暑风物又全然不同。清代阮元写云南的小暑日,居然可以赏菊花,已有夏菊开放。阮元《小暑节赏菊》诗云:
棉衣颇耐午阴凉,瓦盎花开老菊黄。
不是石栏红菡萏,错将小暑认重阳。
诗歌大意说,滇南的小暑节,要身穿棉衣才可以抵挡正午的阴凉,而瓦盆里的黄菊花都早已开放,正可观赏。要不是石栏边上池塘里的红莲花也在盛开,我简直都要把这小暑节气当成了九九重阳节了。
阮元曾任职云贵总督,他另有《滇南小暑节》一诗,诗中明言写于他六十三岁那年,语气是初至云贵总督任上。阮元《滇南小暑节》诗曰:
滇南五月气犹清,云重为阴轻复晴。
非夏非秋别成景,不凉不热最怡情。
棉衣休用蒲葵扇,花院全无竹苇棚。
六十三年惯炎暑,幸将高爽快生平。
云贵同处高原,实则贵州的小暑时节,自当也是“非夏非秋别成景,不凉不热最怡情”,爽爽的感觉最爽爽,真是“幸将高爽快生平”。

除了这些文人诗歌所写的吃荔枝、听蝉鸣、赏菊花,南方民间大都有小暑“食新”的习俗,北方则小暑时节最讲究“吃伏羊”,还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如此说来,小暑时节热倒是真的很热,但总也是美美的,阳光猛烈,高温多雨,作物拔节生长,一切都是那么活力四射,生机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