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贵州高原濮人与僚人的融合及其迁徙
贵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这里居住着苗、布依、侗、水、仡佬、彝,土家、壮、瑶、回、羌等40多个民族。在祖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苗、布依、水、侗、仡佬等民族主要聚居在贵州。贵州高原民族的发展史,始终影响着贵州历史发展的进程。因此,对贵州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以后,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此时,居住在贵州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的濮人、夷人、“五溪蛮”和俚人等各族,纷纷参与了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行列,对贵州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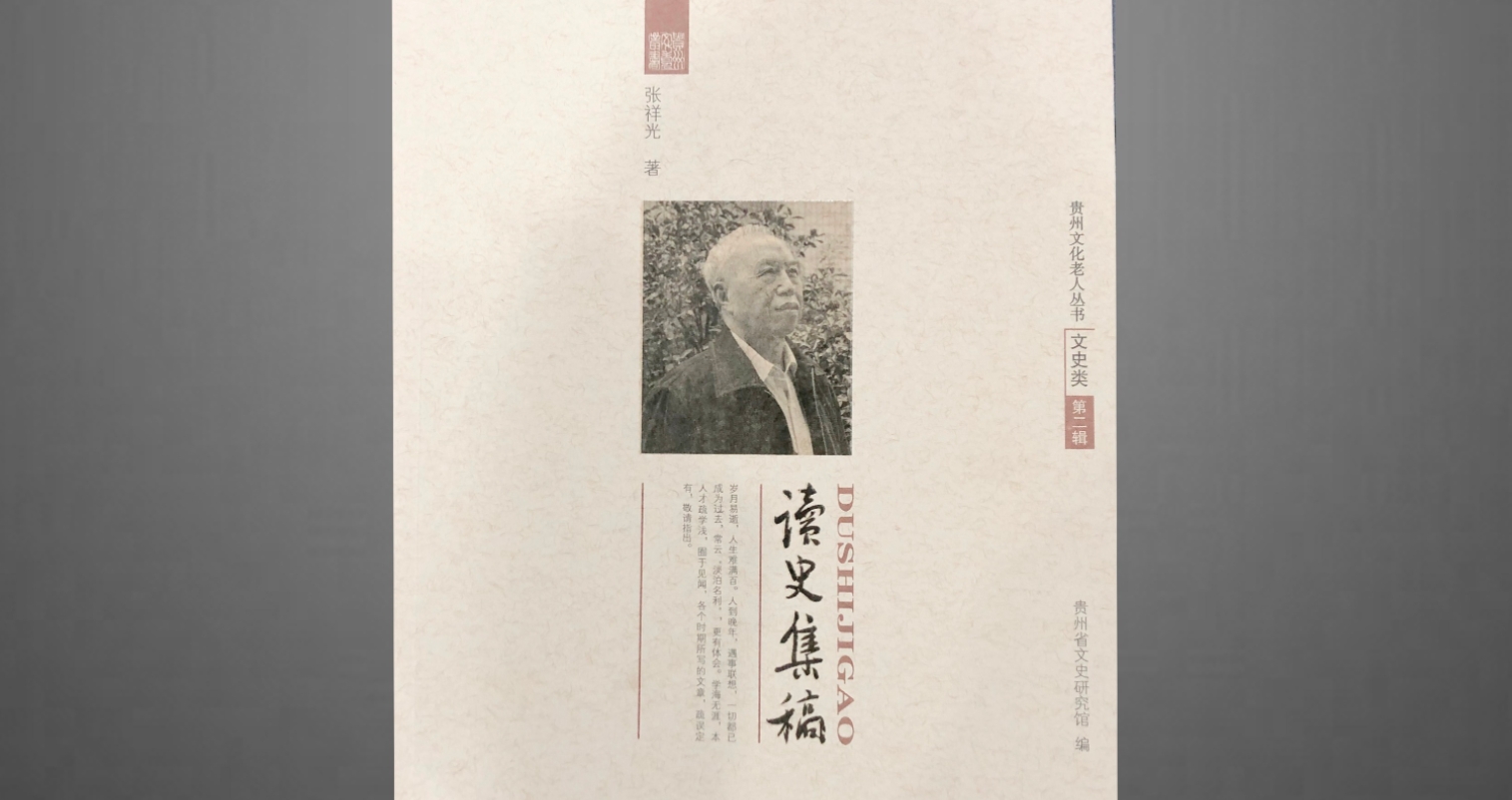
贵州高原濮人与僚人的融合及其迁徙
濮人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之一,分布很广,被称为百濮。至秦汉时期,濮人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降夜郎。夜郎竹王被杀,“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西汉文学家扬雄《蜀都赋》谓:“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华阳国志·巴志》谓:“其属有濮、賨……之蛮。”《华阳国志·蜀志》说:“堂狼县,故濮人邑也。”《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永昌郡)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濮。”从以上材料可知,此时濮人分布区域,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北到四川,都居住有大量濮人。
蜀汉统治南中时,濮人成了受压迫剥削的对象。诸葛亮南征后,以吕凯为云南太守,云南郡人口稀少,“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华阳国志·南中志》)李恢迁徙濮民史籍未记年代,大约是与“赋出叟、濮”这一剥削发生在同时。当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三国志·蜀志·李恢传》)
三国以后,有关濮人的记载逐渐减少,而代之以夷僚或僚的称谓。
僚之称谓出现于史书,最早是陈寿、张华这两个同时代人的著作。《三国志·张嶷传》注引陈寿《益部耆旧传》说:“平南事讫,牂牁、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令(张)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陈寿又在他写的《三国志·霍峻传》中说:“时永昌郡夷僚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峻子)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张华在《博物志》中说:“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上述所谓“僚种”“夷僚”“僚子”,即指僚人。
魏晋以后,濮人并不是突然就消失了,而是汉末以来濮、僚逐渐融合。魏晋南北朝学者认为,濮人即僚人。因此,对同一事件他们或称夷僚、或称夷濮。如发生在夜郎的竹王事件,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南中志》谓:“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牁,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牁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而刘宋时范晔《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则渭:“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可见,“夷濮”即“夷僚”,汉时夜郎地区的主体居民是濮人或僚人。
晋以后,僚人的分布与远古时期濮人的分布相比较,范围缩小了,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域。《博物志》所指“荆州极西南界至蜀",则包括了整个西南地区。史籍还具体指出了僚的分布。《太平寰宇记》卷三百五十六引晋人郭义恭《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郁林、苍悟。”《晋书·武帝纪》:“太康四年(283年)六月,牂牁二千余落内属。”说明牂牁地区僚人主动接受晋王朝统治。此时,牂牁地区社会环境较为安定。到晋末,巴蜀大乱,牂牁地域部分僚人北迁,到成汉李寿之时,“僚自牂牁入”,发生了“引僚入蜀”的事件,“十余万落”僚人进入四川。
史料中记载僚人入蜀的时间,均记载是李寿篡夺帝位以后。史书所记李寿是在东晋咸康四年(338年)称“汉皇帝”,改元汉兴,而在建元元年(343年)“卒”,前后在位五年多。可知,僚人入蜀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40年前后。
僚入蜀后所占据的地方,虽说是“布满山谷”“挟山傍谷”,但不全是益州边远空荒之地。像巴西、渠川、广汉、资中等,都是益州较为富庶之区。因当时李雄起义后,益州许多郡县荒残,无人居住,才被入蜀的僚人所占据。《元和郡县图志》就记载了这方面的资料:“雅州(雅安)李雄窃据,此地荒废,将二十纪,夷僚居之。”又说戎州(宜宾)“李雄窃据,此地空废,后为夷僚居之。”据史料提供的地点,牂牁僚人入蜀后,大体上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等流域之地。
牂牁僚人入蜀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因成汉统治者“骄淫不恤国事,中外离心”,对各族人民施以暴政,在成汉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强迫僚人迁徙。我们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迁徙应是多种因素交叉造成,不可能只有一个原因。故然统治者的强迫在当时封建专制情况下,僚人力量很弱,不可能立即起来抵制,造成了他们屈服成汉政权的压力而不得不迁徙。从史书记载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迁徙彼地(蜀地)的条件;二是自身在牂牁所处的环境。从彼地条件看,李特在公元298年领导流民起义,至李寿时,已近五十年。五十年中,益州战事不断。成汉政权内部为争夺帝位又斗争不休,蜀地人民思乱者“十室而九”,有的逃亡他乡,不少地方成了废墟。如前文所引雅州、戎州就是如此,需要大量的人口补充。从僚人在牂牁当时的处境看,情况很不妙。据《西南彝志》卷六《恒的另一家起源》说:“恒造了兵革利器,计算要征服濮为恒所用……取了濮的九个城。”反映了彝族先民在贵州高原与濮人战斗的情况。彝族先民战胜濮人,而占有其地,至魏晋时期迫使部分濮人向蜀迁徙。
成汉政权“引僚入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成汉政权的灭亡。“(诸僚)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这“十多万落”被彝族先民打败的牂牁僚人,却在益州称雄一世,使成汉政权甚感难应付,成了心腹大患。最后,促使成汉政权迅速衰败。
成汉政权灭亡以后,入蜀僚人继续影响益州局势,当苻坚派人攻打益州时,他们在东晋梁州刺史率领下抵御苻军的进攻。不过,这时他们的称谓不同了,而称巴僚。史载:“苻坚遣王统、朱彤寇蜀,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与巴僚相应,以叛于坚。育自号蜀王,与巴僚酋帅张重、尹万等进围成都。”(《晋书·苻坚载记》)
如果说,他们在李寿时,入蜀后所居住地是“挟山傍谷,与土人参居”的山谷。那么,经过几十年以后,他们已经向城镇迁徙了。《晋书·殷仲堪传》说:“巴宕二郡为群僚所覆,城邑空巷,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为僚有。”殷仲堪在孝武帝(373至396年在位)时,为太子中庶子。他上书指出僚人在蜀地时的势力已很强大、就连巴西、宕渠的城镇,已为僚人所有了。从中可知,僚人势力在益州发展是很快的。
由于在晋代僚人势力强盛,时隔二百年后,《魏书》作者魏收专门为之立传。据《魏书·僚传》所说,僚族的社会形态已进入奴隶社会。而且,买卖奴隶已流行,“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甚至“有卖昆季妻奴尽者。”虽进入阶级社会,但原始社会残余仍很严重,“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其政治组织,有世袭的王,“往往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纺织业有相当的基础,“能为细布,色致鲜净。”其文化特征有干栏、竹簧、铜爨等。干栏本为我国许多民族所共有的居住特征,但是,僚族的干栏既有与其他民族相同点——是一种木桩楼房,上面住人,下面养牲畜;又有僚族的特点,“依树独木,以居其上”,是一种巢居。
总之,从《僚传》所记,魏晋时期的僚人社会经济还处于落后状态。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