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吃贵州丨贵阳人爱烫来吃的木耳菜,滑而柔,是个古老的中国菜蔬


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上周到嘉兴出差,正好找出一本当地老报人陆明所著的《味生谈吃:江南食事别集》,带着在高铁上闲翻。嘉兴没有直达,得在杭州转一趟,整个路程要七个多小时,来回途中,也便很轻松地读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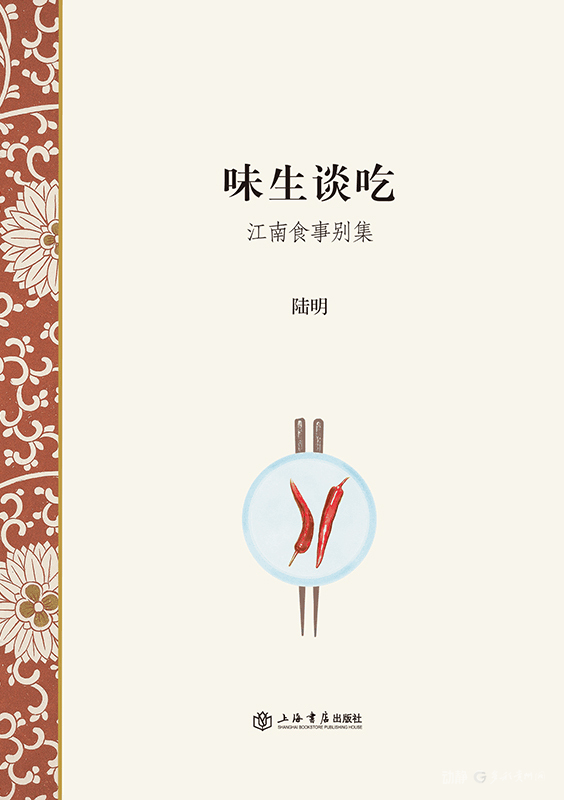
书中有一篇短文,题为《葵之肴》,说是嘉兴人食葵的时间晚近,所以把葵叫做木耳菜,是有差误的。在我的认知里,倒觉得这两者就是一个东西。
话说葵是个中国古已有之的菜蔬,《诗经·豳风·七月》里讲到:“七月烹葵及菽。”菽是豆子,葵也叫作冬寒菜,叶绿而圆,有茸毛,吃起来仿佛有一层粘液。
唐代的白居易写《烹葵》诗,也说“绿英滑且肥”。窃以为,非常准确地形容了葵的口感。
葵菜在中国古代大概是个种植非常普遍蔬菜,据说还不怎么挑地力的肥瘠,甚至四季皆宜。《齐民要术》说它“春者既老,秋叶未生,故种此相接”。什么时候都有得吃。

王祯《东鲁王氏农书》夸赞葵的好处:“葵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供食之余,可为菹腊,枯枿之遗,可为榜簇。子若根则能疗疾。咸无弃材,诚蔬茹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
这也是很切实的评价,今人或以为“白菜为百菜之首”,其实在更长的时段内,中国人吃葵菜要远远比大白菜易得和普遍。
具体到“葵”是什么,《大辞海》的相关条目写得很清楚,“冬寒菜,亦称‘葵’、‘葵菜’、‘冬葵’。锦葵科。一二年生草本。叶圆扇形,稍皱缩。也有叶片皱缩较甚的变种,称‘皱叶冬寒菜’。茎及叶均密生毛茸。夏初自叶腋生出总状花序,开淡红色或紫白色小花。暖地春、秋两季均可栽培,寒地春季栽培;直播或育苗移栽。原产亚洲东部;中国自古有栽培。嫩梢、嫩叶作蔬菜”。
贵州人吃火锅或者酸辣烫,经常能见到葵,或者说冬寒菜、木耳菜。但我也得承认,向来讨厌那种腻刮刮的口感,于是见到木耳菜,多半敬而远之。不过,喜欢的人还是多数,苏东坡甚至说“似可敌莼羹”。
这是个很高的评价了。所谓莼羹,鼎鼎有名,《晋书·张翰传》载:“(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莼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这个典故一直传到现在,那个所谓的“莼菜羹”,至今还是杭州名菜,我十几年前到西湖,第一次吃到,小小的莼菜叶子煮在羹里,淡绿色,清雅宜人,一口下去,滑腻腻的,感觉就是雅致版的木耳菜,还是我从来都不喜欢的口感,不免大失所望。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偏见,白菜葵菜,各有所爱,不必因此掐架。
《味生谈吃:江南食事别集》还写到:“汪(曾祺)先生又说,木耳菜叶小而尖,带紫色。这恰好印证了三个月前我和许岩兄去南湖区书法研究院访友,在小食堂吃到的一盆凉拌菜即是此物。小食堂的主厨告诉我,她只知道此菜叫观音菜,种在花盆里,有十来盆,是从庙里引种的。我好奇,随她去小食堂后的天井里观瞻,木耳菜茎高二尺,枝叶纷披,嫩叶作蔬,摘后复生,取之不竭。观音菜(木耳菜)比较冬寒菜(《诗经》上的葵),糯滑有过之。”
这里我有点稍微不同的意见,因观音菜属于菊科,应该是完全不同的种属,不知为何陆明先生说观音菜是木耳菜,跟葵不是一种菜蔬。但细细揣摩,好像也不值得非要辨析到底,不同地域对于菜蔬的定名,区别很大,各从其是好了。

敝单位的食堂提供烫菜,最近这两周,几乎都配有木耳菜,我偶尔吃到,细细品味,似乎也不像幼时那么抗拒了。大概,是来自于文字描写的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