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我的家庭教育
该文选自《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一书,此书乃是陈祖武先生自述其一生学思心路历程,由王进教授采访录音,并反复认真领会整理,贡献给学界的一份当代学人思想文献礼品。让我们紧随陈祖武先生之后,感悟他治学的持恒与辛劳,感受他用一生精力构建出来的学术宫殿和他一生始终不渝的学术职志和人品风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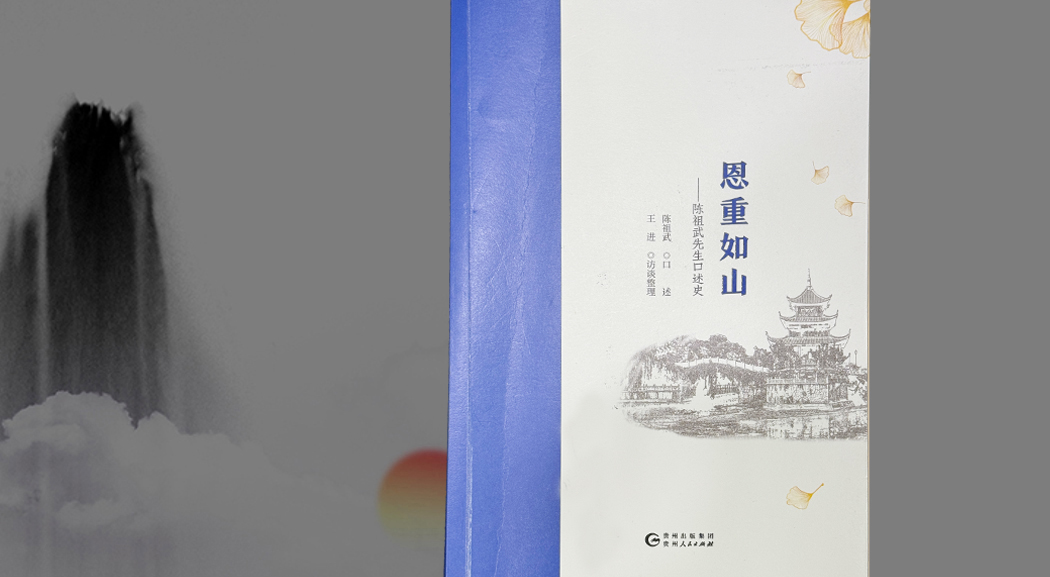
我的家庭教育
我的祖父和母亲奠定了我人生最初的教育。
祖父是个非常慈祥、和蔼、敬业的老人,我有一个哥哥和姐姐,我排行最小,祖父很偏爱我,他经常把自己喝的牛奶和肉圆子有意留给我。当我懂事和能够做事时,每天一早吃完早餐后,就给祖父磨墨,然后远远地看着他给病人号脉和写方子。没有病人的时候,祖父就给我讲书。尽管我们家有很多医书,但他讲的不是医书,而主要是单行本的《论语》。他教育我要好好念书,好好做人,才不至于枉来人间。为什么祖父不给我讲医书、讲医术,而是讲《论语》?我想这或许是祖父的深远考虑。我们知道,无论是医术还是其他的技艺,都根基于人。人的品德和修养,决定人所做的事的大小和品质。“术”源于“心”,没有关爱他人的“仁心”,也就没有良好的“仁术”。
我们家门口挂有一块很大的黑底金字匾额,镌刻着“是乃仁术”四个大字。我看不懂,就问祖父是什么意思。祖父给我讲“仁”,讲“爱人”,也就是友爱他人。他说,“像我这样为他人治病,病人根据我的方子吃药后好了,这就是‘仁术’,也就是‘仁爱之术’”。祖父告诉我,你从小要爱人、关心人,要懂礼节。祖父很关心体恤劳苦百姓,很多时候,他看到病人没钱,也就免了人家的费用。
祖父一生行医,但我一点也没有继承。即使是今天我已经年老,但对很流行的“养生”既无兴趣,也无了解,但是祖父“医者”的形象和“仁者”的风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可以说,祖父不仅给我们的大家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给我的一生奠定了厚实的根基。
祖父还培养了我一生的读书习惯,也可以说这是祖父留给我们的“家教”。在读书方面,他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在我的印象中,只要没给人看病时,他都是拿着书,可以说是“手不释卷”。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也养成了从小喜欢看书的习惯。当然,这也与祖父的有意培养密切相关。我有一个兄长,长我四岁。很小的时候,祖父就在他的书房里安排位置,让我们写字、看书。等我们长大以后,又给我和哥哥专门辟出书房。我们的书房里摆着“敬惜字纸”的字样,告诉我们要爱惜文具纸张,不能随意乱丢。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受到读书的重要。
我们常说“言传身教”。祖父当年给我讲解《论语》和“是乃仁术”,以及母亲的教诲,或可谓“言传”;而祖父行医的仁爱风格和母亲的勤劳节俭,或可谓“身教”。这构成了我最初的启蒙教育。
这样的教育与后来我上学读书所接受的“‘五爱’教育”前后接续,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一生为人做事的基础。

陈祖武,生于1943年,贵州贵阳人,全国著名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专长为清代学术史,个人专著主要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代学者象传校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