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故人具鸡黍”里的厚意与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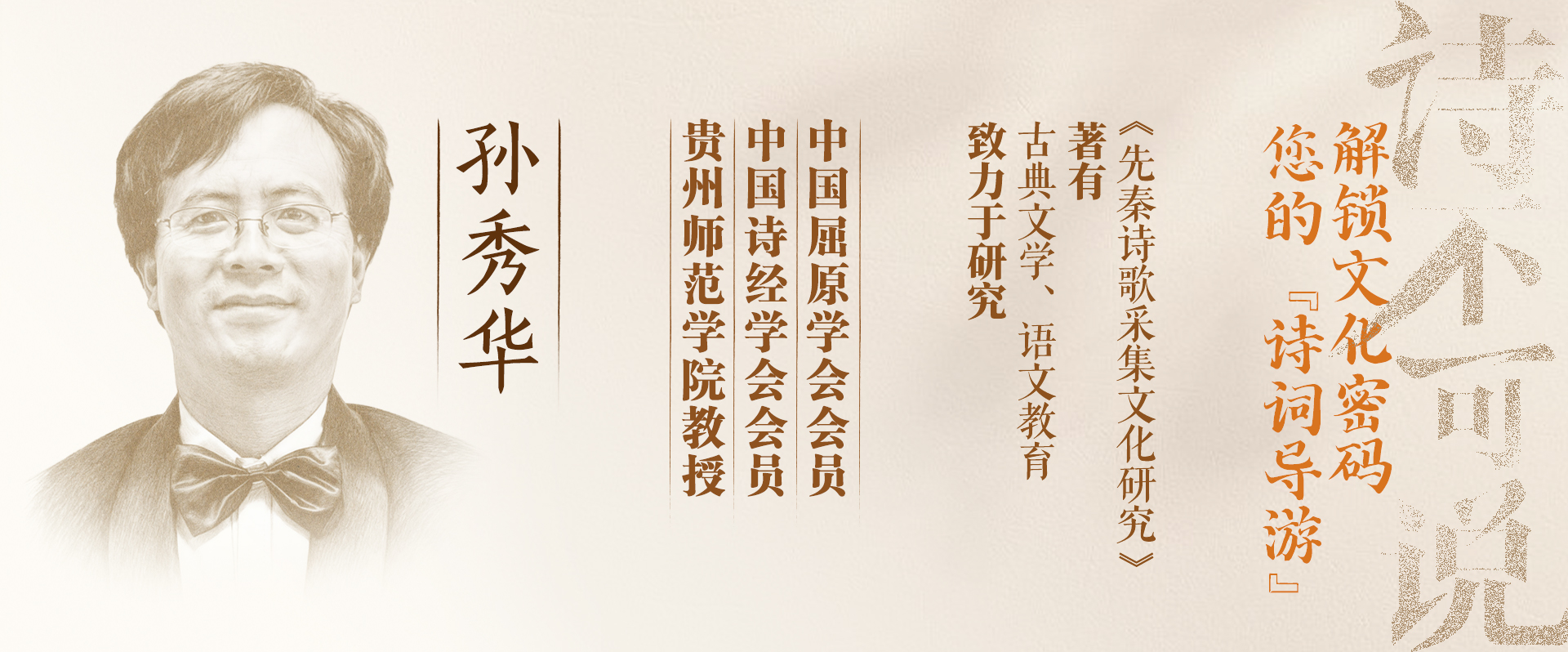
孟浩然《过故人庄》诗云: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单论首联“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主人以“鸡黍”相邀,平静而自然,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客人应邀而至,招之即来,可见友情深,知交久,不讲虚礼排场。
而深入探究,远不止这些感受,看似平淡的诗句“故人具鸡黍”,实则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记忆。

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吃到鸡黍饭晚餐的“史上第一人”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受招待于“荷蓧丈人”。故事见于《论语·微子》第七章: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荷蓧丈人是孔子认定的“隐者”,尽管荷蓧丈人完全不认可孔子师徒的处世之道。而故事里荷蓧丈人“杀鸡为黍而食之”招待子路,并安排自己的两个儿子与子路会见,是尤其隆重的正式的社交礼仪,还不仅仅只是吃一顿晚饭而已。
另一个大家熟知的鸡黍待客典故来自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热忱待客的是桃源中人。《桃花源记》写到,当武陵渔夫进入桃花源,桃源中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下文还说,“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陶渊明爱酒,此处的“酒食”也便是上文“设酒杀鸡作食”的简称,而尽管陶渊明并没有明确说这“食”是黍米饭,但即便招待完全陌生的客人如武陵渔夫,主人们依然郑重其事,热情如火,心意满满。

区别于热情接待陌生人,以鸡黍待客,客人是老朋友“故人”的,最著名的故事甚至凝炼为成语“鸡黍之交”。
“鸡黍之交”典故源自南朝宋代范晔所著《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式传》中的范式与张劭故事: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故事说,东汉山阳金乡人范式与汝南人张劭是“太学”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分别之时,范式约定二年后到张劭家拜访。“信士”言出必行,约定之日,范式果然如期而至,升堂拜饮,与张劭尽欢而别。
而《范式传》下文还有很长的内容,其中突出了范式是张劭的“死友”,“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张劭病逝前称唯有范式能履生死之诺,范式闻讯白衣奔丧,张劭灵柩因待其执绋引柩方得入葬。因而“死友”一词,特指交情甚笃、至死不负的朋友。范张“鸡黍之交”的内涵,也从生前的守信延伸至死后的不离不弃,将友情的诚信提升至超越生死的境界。故而范式与张劭“鸡黍之交”,成为诚信守约、信义昭著的典范,对后世影响巨大,甚至凡诗词文赋中谈到“鸡黍”,均指向如此诚挚的君子之交。
而尤为值得指出的是,事实上,原典《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式传》里,居然根本没有提到“杀鸡为黍而食之”,“鸡黍之交”典故里全然没说什么“鸡黍”。也即,是后世文人全都自觉默认张劭招待“死友”范式的必定就是“鸡黍”——呵呵,这简直就是“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但再审慎反思一番,却又不由不让人叹服,春秋时期便载之于典籍的鸡黍待客仪式里的厚意与深情,让“鸡黍”成为了不二之选。要不,你说,张劭拿什么招待了范式,那肯定就是“鸡黍”啊!
而从符号学的视阈看,当“鸡黍”从具体的历史故事中抽离出来,也便逐渐演变为一个承载着传统文化精神的能指符号。每当诗人使用这一意象,便不仅仅是描写一顿普通的饭菜,而是在召唤一整套关于诚信、友谊、田园理想的文化密码。这种符号化的过程,使得“鸡黍”意象能够穿越时空,在不同时代、不同诗人的笔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探源辨流细梳理,再回味孟浩然《过故人庄》之诗句“故人具鸡黍”一语,则蓦然觉得,开篇就提到了“鸡黍”意象,赋予了诗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首联“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既是对眼前场景的真实描写,又是对历史典故的暗中呼应。如此一来,这里的“故人”不再只是普通朋友,而是承载着如范式与张劭那般深厚情谊的知己之交;“鸡黍”自然也不只是普通的现实里的饭食,而是饱含昭著信义与真挚情谊的精神世界里的文化符号。
当然,孟浩然在诗中并未直接提及范式、张劭之名,也没有叙述《后汉书》中的相关故事内容,而是以含蓄隐晦的方式化用典故,使不了解背景的读者能够欣赏诗中的田园意境,而了解典故的读者则能领会更深层的文化意蕴。通过这种隐约含蓄的用典,孟浩然将历史典故、个人体验与田园理想完美结合起来,使得这首诗作既是个体情感的抒发与表达,也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再现与升华,体现了其“言近旨远”的美学追求,也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如何将历史典故转化为诗意表达的完美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