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山漫记∣《矩州风物——青春一页(外三篇)》
作者:涤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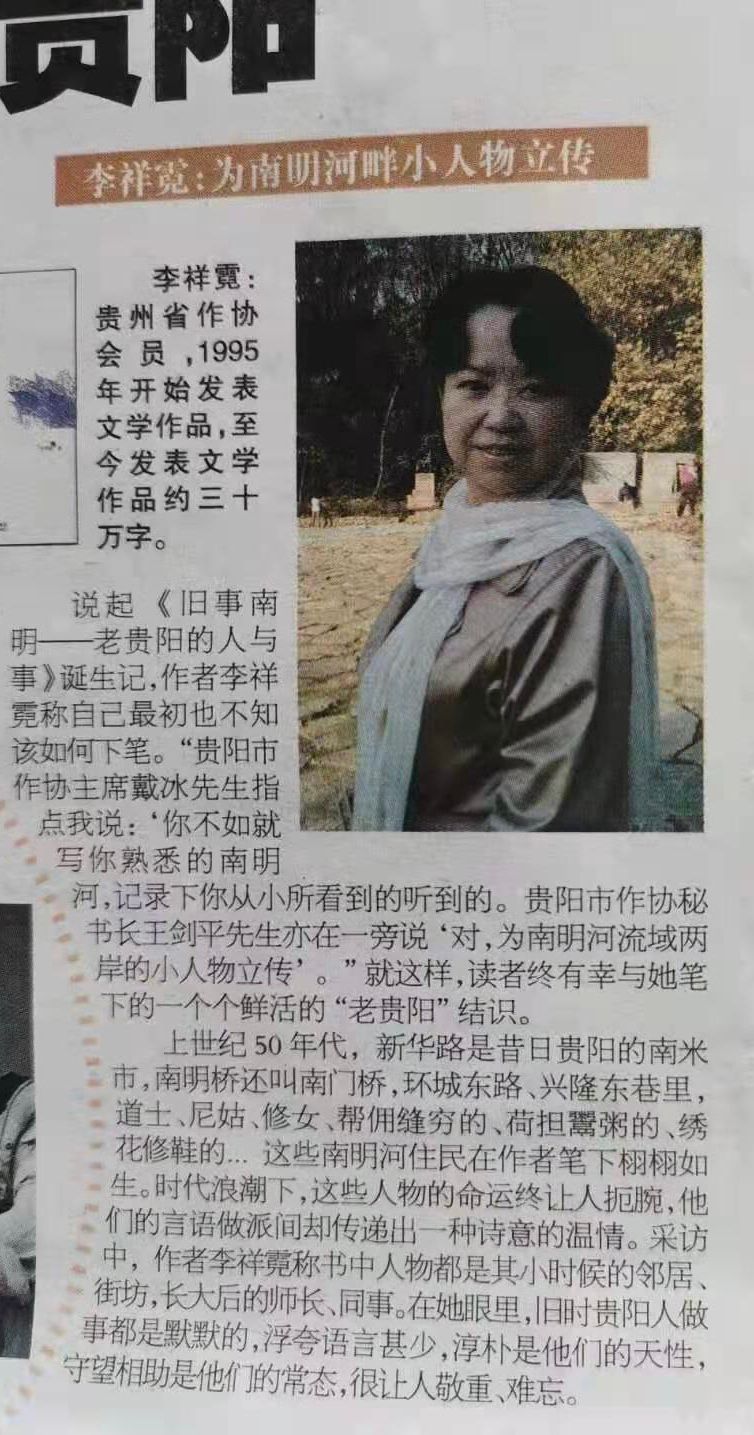
青春一页
从贵阳乘火车到凯里,在列车进站前,要经过最后一个隧道——插旗山隧道。
1971年6月后,修建湘黔铁路的贵阳市学生团的学生们,几乎天天都会有几个、数个、数十个,手擎着火把,进出于插旗山隧道。我,亦是其中的一员。
1971年6月,在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下,贵阳市号码中学老三届、新三届的回城知青、待校生计2万名左右,在市革委会的领导下,组成了“修建湘黔铁路学生团”,来到凯里“湾溪”,开始了修建湘黔铁路的营生……
贵阳九中,编制为二营七连,一、三排为男生,二排为女生,我在二排。
到湾溪的当天,大家从砍树、割茅草、搭工棚,起早贪黑地干了半个月,终于,我们140多号人有了吃喝拉撒睡的地儿。
真好,多亏我们连那些下过乡的男知青们,他们总是拣诸如砍树子、扛木头、改方子、锯板子、搭工棚等最苦最累的事做,我们只是在山腰上挖地基,夯平地。他们对小同学默默无言爱护、礼让,使第一次远离妈妈的我倍感温暖。
就在大家雀跃着从“天作房,地当床”的窘况中搬进新工棚的当天,一整狂风将我们的工棚顶掀得没了踪影。真真是“风如拔山努,雨如决河倾”。顷刻间,我们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女生们的脸上已分不清是泪是雨,男生们则静静地伫立着,淋雨。
是夜,“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
第二天,太阳当空照。男生们齐心合力地修补工棚,女生们则不分彼此地晾晒着大家拧得出水的铺笼帐盖,满山遍野呼喇喇地招展着同学们的五色旗,年轻的我们唱着跳着叫着喊着,昨天的阴霾一扫而光。
许是那时年少无心思?又或是来到湾溪修铁路的学生们“底牌”都尔尔?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团结友爱、同甘共苦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情愫。
学生团的任务,是搬掉横亘在插旗山岭的一个山谷。为了争时间,领导决定采取大爆破施工。大爆破工程有17个导洞和23个药室,我们连的任务是打通4、5、6号洞。谁能想得到,这些平均年龄19岁的孩子们,竟然要炸掉填平一座山?
大会战开始了。连里勇敢的男生毛遂自荐地腰拴着麻绳,手拿着錾子,在悬崖峭壁上先錾出可以落脚的地儿,再一人手握钢钎,一人手抡大锤,一锤一锤地凿出了一个个洞的雏形、一条从山下至山上的路。紧接着,掌握钢钎的男生配合着锤子的韵律转动着钢钎,坚硬的岩石就这么一点点地被錾成一个个炮眼。当炮眼的深度达到要求时,将炸药塞进炮眼,把引线牵到洞口;班长叫所有人都远离洞口,然后点燃引线,三步两步地跑到我们身旁,大家双手蒙住耳朵,大约一分钟后,只听得嗡的一声闷响,我知道,这次推进洞深度的爆破又成功了。
虽然才入秋,可大山里的气候阴冷清寒,令人瑟瑟。我穿着一件“棉猴”,身背着药箱,穿梭于各个洞之间,为受伤的战友擦药包扎。打炮眼的工作又累又险,受伤的基本上都是打炮眼的男生,女生只做清渣工作,所以不曾有人受伤。
在工作间隙,我随意靠在任何一个洞口休息,一有伤员叫唤,我就会奔过去处理伤口。推渣的鸡公车在我面前进进出出,女生们看我坐着不动,就给我取了一个外号“菩萨”,为此我神伤了好久。虽然我觉得各司其职我没有错,但“菩萨”名号让我抬不起头来。有些男生为我打抱不平,安慰我说“有菩萨为我们守卫,我们在里面打洞觉得安全。”有些干脆就大声大气地在洞内叫唤,说谁谁谁受伤了,要我进去包扎。结果亦是为了保护我佯装受伤的。我还得假模假式地在其完美的皮肤上涂上红药水,再缠上绷带,对方竟得意地吹着口哨走到洞口,自称轻伤不下火线,只吃病号饭就行了。我羞愧难当,此类事发生两次之后,我于心不安,自动放弃了卫生员的工作,加入了清渣队伍。
在日复一日鸡公车叽咕叽咕的清渣工作中,我变得坚强勇敢起来,虽仍然穿着“棉猴”,却没有人再喊我“菩萨”了。
妈妈来信说,我们连长家访时说我“体弱思想红。不要急,慢慢锻炼就好了。”我不领情地恨“锻炼”两个字,大家一样工作,为什么就我算是锻炼呢?!
终于到了大爆破的这一天。
1971年12月28日清晨,执行团里的统一分配,我们连每人带上俩馒头,站在另外一座山巅,远眺着半年多以来日夜工作的4、5、6号洞。每个洞的药室都填满了炸药,引线全都汇同连接上了其他连队的十几个洞。
下午两点整,第一声警号响后,山上人人都屏住了呼吸,个个都听得到相邻同学的心跳;奇怪的是,连被风吹得左右弯腰的树叶,竟然都是静悄悄的?
总指挥最后一声哨子响过后,万籁寂静。倐地,轰……一声巨响,一束巨大的红光从山腰处喷发出来,红光抬起了整座山峰;霎时间,一团巨大的白紫色雾直冲云端,我们天天相伴的山岭不见了,瞬间就变成了平地!
贵阳学生团的第一项任务圆满完成……
或恐是同乡
“君家居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少时在北京偶遇一贵阳男孩,一定要问人家是否住南明河,还一知半解地背了这首诗。那男孩被逼得憋了半天才憋出了一句:
“我家没得住南门河,我家住在杨家大河。”
“南门河,南门河!是南明河不是南门河。”
我凶巴巴地更正,觉得人家玷污了南明河,还自以为是地说:“杨家大河就是南明河。”其实,肤浅如我,无知自我。
南明河穿过甲秀楼处自古就有着“九眼照沙洲”美誉的九孔浮玉桥,流经东岸贵州省委所在地南明堂与西岸杨河沟(即石岭街)一段河道,称为“杨家大河”。这一段得名为“杨家大河”,据说是明万历24年生于贵阳城南郊南明河畔的石林精舍、后中举移居南京,诗、书、画三绝,与董其昌、王时敏等大家齐名,合称“金陵九子”之一的杨龙友(1596-1646)家的属地,故名为 “杨家大河”。虽然如今都统称为“南明河”了,但当地老街坊仍然称之为“杨家大河”。
杨家大河深又长,
清清亮亮洗衣裳。
我家住在河岸边,
天天闹水河中间。
杨家大河宽又绵,
东边画楼西边田。
黄墙绿瓦坐大官,
碧水桑田任我涎。
在杨家大河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都是唱着这些童谣长大的。
儿时的杨家大河,是我们神秘美妙的天堂……
东岸,深掩在白杨梧桐深处的南明堂,黄墙绿瓦的建筑群楼台深锁、高贵肃穆,令我们西岸小孩个个高山仰止;每每凫水到此,楞是不敢“到此一游”,只会叽叽喳喳地猜测里面的是“哪路神仙”。每当看到楼廊里有人影走动,吓得一个鹞子钻进水里,只敢去和打鱼老汉的鱼鹰抢鱼。西岸则是我们的天下,岸上的第七幼儿园、甲秀小学、第九中学均是我们的母校,岸边的喇叭花狗尾草,乱坟古墓塔、包谷杆胡豆心皆是我们的故事源泉、解馋的美食;我的乔木灌木、木犀科蔷薇属等植物知识,也是在这儿首度领知……
我们长大了,南明河也长大了;我们有了忧伤,南明河也有了忧伤……
我们改革开放了,南明河也笑逐言开了……
东岸的白杨梧桐依然高贵肃穆,黄蔷绿瓦却不再楼台深锁。作为贵州省委办公驻地的南明堂,架起了一坐东西两岸连接政府和老百姓身心的桥——冠洲桥。西岸上的幼儿园、小学、中学,乔木灌木、木犀科蔷薇属依旧当年,只是更加书声朗朗、郁郁葱葱。归置齐整的南明河水碧绿清凌,河边高楼林立、鸟语花香,两岸游人自由呼吸、来来往往……
八十年代在北京读书时,一次在颐和园写生,忽听得一阵喧闹,其中还夹杂着凶巴巴的贵阳话,他乡遇故音!还禁得?扑爬礼拜地赶过去——几个贵阳的青年和北京“爷们”正相互在褒贬着自己和别人的家乡:
“你们贵阳穷山恶水的,天无三日晴……”。
“你们北京有什么好?一条金水河,还是短拙拙干巴巴的,又不能游泳。你见过老子们南明河没得?哼!可以游穿城噢……”
我急忙上前询问那伙贵阳人:
“你们是贵阳的?住在南明河?”
那几人也顾不得用普通话吵架了,和我对开了贵阳腔:
“我家住小车河。”
“我家住甲秀楼。”
“我家住杨河沟。”
我激动得喉咙都干了:
“我们都是南明河的老乡啊!”
大伙欢呼起来。霎时!一场吼架,化为痛快淋漓的开怀大笑。
曾几何时读到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若是大侃什么,你会嗤之以鼻。
若是吹虚他的家乡,你会为他动容。是这个理儿!
若许年来,只要身处异地,一听贵阳口音,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上前搭讪,嘘寒问暖,临了还会作揖戏谑:
“君家居何处,我住南明河;停步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对方亦会欣喜地道:
“都住南明河,肯定是同乡喽!”
互道珍重后,相约贵阳再见。
南明河,一条穿越贵阳城的妈妈河,让我们同乡遍地,亲情满天。
“求”胆南明河
南明河段的“大蚜凼”和“小岈凼”之间(今贵州省委至贵阳第九中学一段叫“大岈凼”, 贵阳第九中学至今冠洲桥段为“小蚜凼”),是我学会游泳的地方,教练是我妈妈。
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的一个下午,我随妈妈到南明河洗衣服,妈妈没有像平时一样一到河边就开始洗衣,而是从盆里取出一件看似我读幼儿园时穿的荷叶围裙。抖开一看,哈,一件游泳衣(可不是我的苏联式围裙?经隔壁唐老师加工改良成的游泳衣——我今生见过的最美的游泳衣)!女孩子再小,天生就懂得害羞。所以,没有游泳衣的日子即令再羡慕别人在河里嬉戏,我也没有下过河(至今我都不知道妈妈是何以得知我想要一件游泳衣的)。可想而知,我见到这件有着蕾丝荷叶边的游泳衣时是怎样地欣喜若狂。
我在妈妈身穿的“布拉吉”下换好了游泳衣,兴奋着梭下河扒在一块大石头旁不敢动弹。妈妈又在盆里拿出一个褐黄色扁椭圆形的东西,用嘴往里吹气。一会儿,妈妈手里就变出了一个椭圆形的球。我惊喜万分地接过这个橡皮椭圆形球,妈妈说,这是篮球的芯,叫球胆,可以漂在水面帮助你学游泳。接着,妈妈把我牵到齐腰深的水里,教我用两手捧住球胆,让我试着在水里闭气,说是握紧球胆我就会在水面漂起来。我因为胆小害怕,几次都漂不起来,妈妈说:“不要怕,大胆点,球胆会帮你浮起来的。我也是这么学会游泳的,你肯定也学得会。”说完,妈妈转身洗衣服去了。
扑沉下去又挣扎起来,呛了水又吐干挣。一南明河的水都被我搅混了,我终于没有漂起来。
妈妈洗完衣服看了看浑身泥浆的我,哗地笑开了:“咦,哪儿来的小泥猴哦?喏,看我的。”
妈妈把两根长辫子盘在头顶,穿着“布拉吉”就跳到了河里:天蓝底白玉兰花面料的“布拉吉”载着妈妈在水面上漂呀漂的,南明河面上顿时开满了玉兰花。我羡慕地看着妈妈在河中央一会儿蛙泳,一会儿仰泳自由自在地畅游,我更是再也漂也漂不起来了。妈妈没有再强求我。上岸以后,妈妈穿着湿漉漉的“布拉吉”,端着衣服,一路给我讲着胆大飘洋过海至今在美国的大舅和胆小寸步难行后来身陷囹圄的二舅……
后来的一天,妈妈下班回家告诉我们,她要去南明区校、园长“学习班”学习,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是保密的,不许乱问。妈妈告诫我和妹妹不要出去野,更不要下河。那晚,我睡在床上,听见妈妈在轻轻唱着她经常唱的那首苏联歌曲:“哎……哎……/你阴暗的阔叶林啊/请你给我让出条小路吧/我的心里充满了忧愁悲伤/使我看不到明朗的天呀……”我听着妈妈的歌,心想,我一定要学会游泳让妈妈高兴。第二天,妈妈就走了,都翻年的冬天了,妈妈还没有回来。
就在那年的夏天,我用妈妈给我的球胆,在南明河里学会了游泳。我是在跟几个小孩抢球胆的时候真正不依赖球胆凫出水面的,同时,我也失去了妈妈给我的球胆——在抢到球胆时,球胆已经五零四散了!
真正的玉兰花开的时候,妈妈回来了。没有了“布拉吉”,没有了长辫子。我告诉妈妈,我已经会游泳了,是用她教的方法学会的,只可惜,球胆没有了!妈妈笑着点点我的胸口:“球胆还在的呀,在你身体里了。”我半天才反应:“嘿,真的是这样嘞!”
南明河水日夜流,流去不回头。妈妈也随着南明河水流走了……
如今,我在南明河边看到小孩们在河里学游泳,我就想起了那个球胆,可竟然没有当初的那种懊恼,却觉得心里柔柔的,就像绵绵的南明河水一样。我突然读懂了普希金的那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伤,不要心急,
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就要来临。
心永远憧憬着未来,
现在一切却是沉寂。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童谣趣谈
贵阳多元的人源,决定了贵阳童谣的多元。喏:抗日战争时期来的、南下来的、支黔来的、三线建设来的;一拨一拨的东西南北人,带来了一首一首的南腔北调文,仅仅就“童谣”,就能让贵阳各年龄段的孩子们大受裨益。
土地公,土地婆/吃我斋饭保我禾/今年保我千千担/明年保我万万箩。
这是我外公留下来的“传家之宝”——江西丰城童谣“求土地”。
外公是江西人,年轻时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结识了贵州革
命党人张时祺、黄石钦俩先贤,遂到贵州。虽然已经三辈人定居于贵阳,带来的身家性命亦只留下了家乡童谣,但刀断水更流之故乡情,已成为我们家的根源念想,因此,我们家族几辈人的小孩都会念。
还有一首:高高山上一座楼/两个人在打拳头/拳头打,打拳头/那边来了一个人/看他们两个打拳头/拳头打,打拳头。
这是俩小童一起玩的童谣“对持”。最妙的是,俩小童念完上一段后,接着又是“那边来了一个人/ 看他们两个打拳头/拳头打,打拳头”此三句就周而复始地念呀念,直到不想再念或大人喝令“打住!”
我父亲是抗战时随浙江大学西迁来贵州的一年级学生,他的浙江童谣也与他一起根落贵阳。小时候父亲一说起家乡,首念的就是杭州风景童谣:
一线天,二老亭/ 三生有缘石上见。
四眼井,五云山/ 六和宝塔立江边。
七星缸,八卦田/ 九里松月照清泉。
十锦塘,百子尖/ 千人洞里去探险/ 万松岭上共醉眠。
还有老家的生肖童谣——
老大细,老二大力气,老三吼声大,老四藏山旮,老五贴天穹,老六盘路边,老七落教场,老八好温良,老九猢狲形,老十叫天鸣,十一喂不饱,十二供神道。学会“生肖童谣”,随口就能背出十二生肖的顺序,还捎带着背得了“天干地支”。划算,背一得二。
我大哥、小哥看《三国》时,两人总爱对书中谁打仗最凶突起争端。父亲教他俩念“三国”中武将座次的童谣,说会念该童谣,就能记住整本《三国》。谁曾想,最先背得“三国童谣”的不是作文写得好的大哥,而是专为同学做数学作业当了班上“大王”的小哥。好容易胜了大哥一筹的小哥还将“三国”中24位武将的名字标明给拥戴他的同学。据此,小哥得了个绰号“三国通”。大哥嗤笑小哥顶多是记住了姓名而已。小哥不服气,用毛笔将“三国童谣”写在一大张白纸上,贴在我们院子里天天都有人经过的走廊墙壁上。结果,院子里的小孩都会背诵了。以下就是“三国童谣”连同小哥的标注:
“一吕二赵三典韦(吕布、赵云、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关羽、马超、张飞),黄许孙太两夏侯(黄忠、许褚、孙策、太史慈、夏侯敦、夏侯渊),二张徐庞甘周魏(张辽、张颌、徐晃、庞德、甘宁、周泰、魏延),神枪张锈与文颜(张锈、文丑、颜良),虽勇无奈命太悲,三国二十四名将,打末邓艾与姜维。”
小哥肯定想不到,文革中他的“杰作”亦为我们家添了一桩“大力宣扬黑书、大毒草”的罪状。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夫家籍贯山西,公公婆婆都是南下来的。当年一匹毛驴架着俩箩筐,一边大姑姐,一边大伯兄,一路嘎吱嘎吱地进军川北至贵阳,从此落地生根。我那总念叨山西这么那么好的奶奶,一抱起孙子天天念的就是她们山西孝义的童谣——
洋囡(山西人读nu努音)派,摘花来?
花呢?卖钱了?
钱呢?割肉了?
肉呢?猫吃了?
猫呢?上树了?
树呢?水淹了?
水呢?龙喝了?
龙呢?上天了?
天呢?塌了?
吓得小姐圪溜了?
一句山西人话语中不可或缺的“圪溜了”,道尽了远离家乡游子对乡土乡音的恋恋乡情。每次奶奶一念,即会引出爷爷念,我孩子几乎是会讲话就会念了。我?当然会啦,还传承给了娘家人了嘞!
哦!童谣童谣
爷爷的烧酒奶奶的饭
外婆的油茶外公的担
喝着酒,吃着饭,呷着茶,挑着担
噹唧噹唧念的欢
念甚嗫?
眼里有,心里有,口里更有我的乖
什么嘛
童谣乖乖哉
嗙唧嗙唧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