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空间·叙谈录丨家政女工拿起了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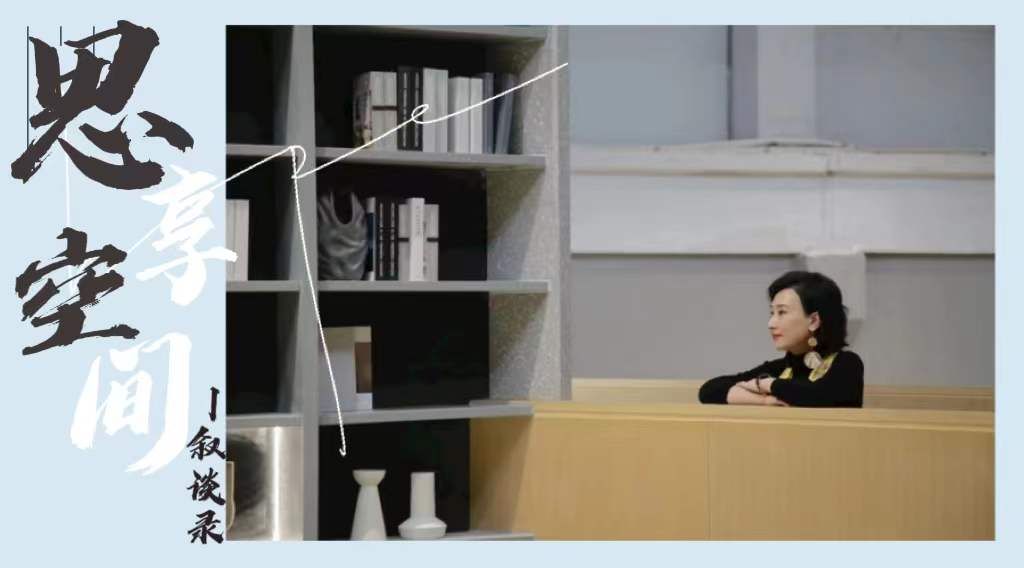
这是一群看起来几乎与写作无关的女性。她们大多中年,从农村来到城市,住进不属于自己的家里,做着家务、照顾幼儿或老人。作为家政工,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时间也几乎全都交给了别人。
当这样的一群女性拿起笔,她们首先会写什么?出乎意料的是,她们在赞叹生活的美好。看似辛苦、艰难谋生的生活,是她们获取收入、拥有较为独立生活和身份的难得方式。
但真正的写作不能停留于此,它还关乎你如何去看待自身以及自身所遭遇的一切,你要去写出生活里更丰富但也更复杂的面貌。艺术家静远给她们上过写作课,除了告诉她们「每个人都可以写作」之外,她还说,写作的实质是「我需要面对自己,需要面对现实」。

《住在亲情里的疫情》已经出版一年了,一年后静远再回过去看,发现了一个有点「蹊跷」的事情:她认识的一些人,城市中产女性,她们对书里的故事非常有共鸣。
静远第一反应是,为什么你会有共鸣?你又不是跟她们一样的生活轨迹,也不是跟她们一样的现状。但是她们会觉得,她们跟母亲的关系、情感,在这本书里得到了一个完全的解释。她们是真心共鸣,包括心中那种焦虑和不安全感,还有作为一个女性,在压抑之下,很想去向外去连接、去求救,想改变自己生活的冲动,这些似乎是被联系得最多的情感。
不同出身的女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书里有很多地方提到这样的情节。梦雨说,她不希望女儿被她的丈夫、婆婆催婚,她希望女儿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但是她的女儿因为是由上一辈人养大,和上一辈人观念更近。所以,梦雨会觉得自己很无能,很无力。
书里有杨暮的故事,她是北京的一个家政工,小时候经历了父母的离异,长大之后特别自卑,结婚后,她的公婆对她不好,她都忍受了,她对儿子有很多的期望。有很多城市中产女性从这个故事里获得共鸣,她们觉得自己的母亲也像杨暮一样,人生转折都是被命运推着走。

三年前,静远跟家政女工一起做项目的时候,她只是从自己的身份出发,对某一类人群感兴趣。三年里,她看到了其中重要的社会意义。更重要的是,三年过去了,静远跟她们建立了友情,也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她们让她更坚强。静远接触到的很多人,包括自己,会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什么用。但是跟家政女工接触,会看到她们背负了很多的责任,一直在面对具体的事情。
她们显示出很不一样的生命力。她们更宽容,这宽容里当然也包括了隐忍和妥协。在她们的生命里,很少有具体的鼓励,活下去就是她们的韧性,但她们不会很具体地恨,也并不麻木,她们会为很小的事情开心。她不一定脑子里有所谓的社会、社区这样的词语,但是她们会去做,比如雁子,她主动影响她认识的人,向别的女性推荐图书室和绘本教育,她能给就给。

写作是她们的新工具,她们尝试有所表达,尝试以后还要去检验它和现实的关系,这个严肃、完整、独立的思考过程,就是创造。这个时候,她们就可以说:我在说话,我在向世界说话。
——戴敏洁
文本参考:《人物》 作者:戴敏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