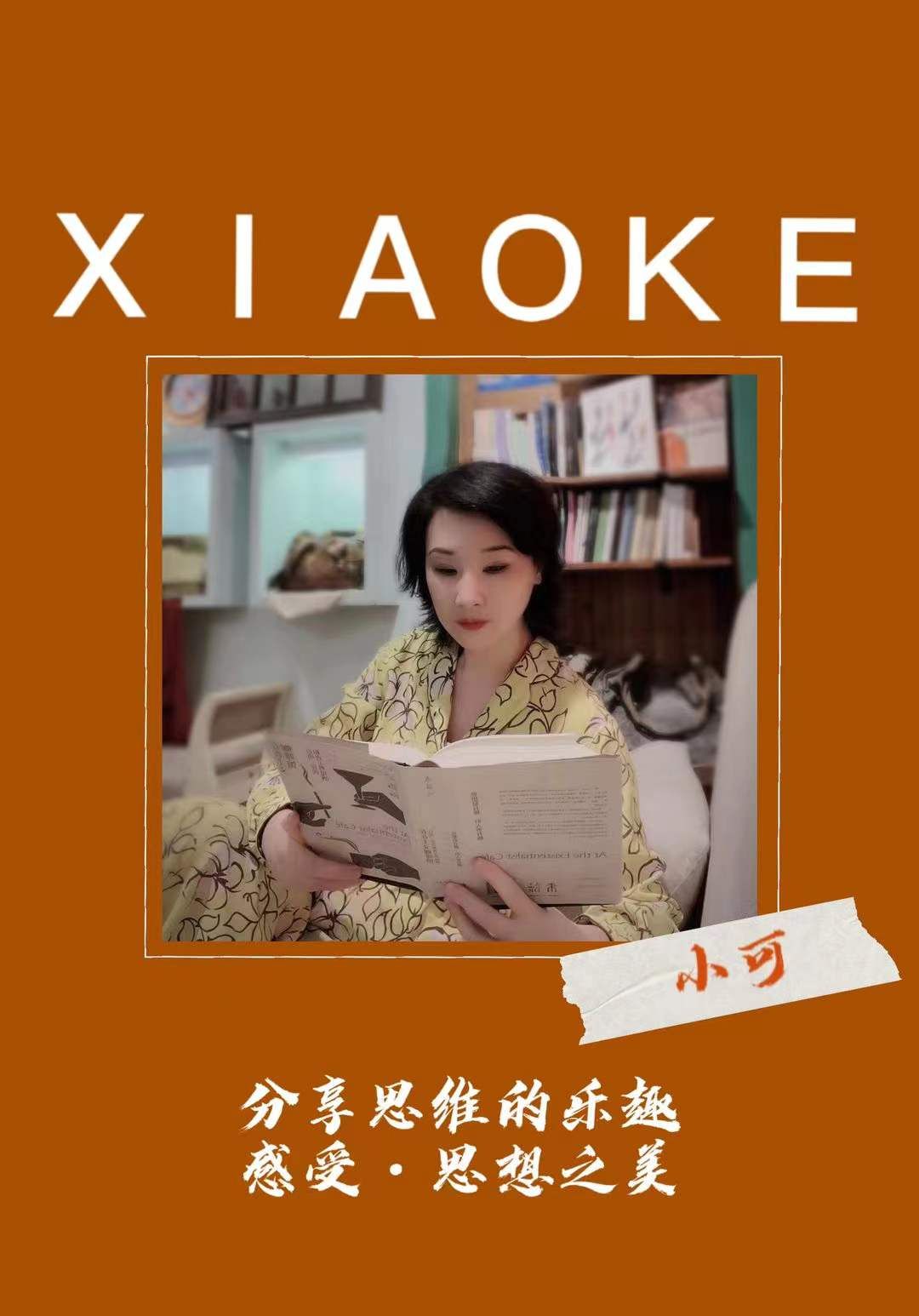思享空间·人物志丨沈大成——我不是糕团店,我是个作家


沈大成,上海一家知名糕团店的名字,去南京东路逛街的人大都见过这家门店,它卖鲁迅爱吃的条头糕,还有双酿团、青团等美味糕点。
徐晓倩,1977年生,上海人,她说自己很喜欢吃沈大成的黑米糕,又想取一个中性化不辨雌雄的文学笔名,就拿来用了,她说:“名字会泄露很多秘密的。而且,我本身不擅长社交,这个笔名,别人跟我聊天的时候,总会问起,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关于沈大成的那些事——写奇怪的人
沈大成的小说不太写人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你我他、ABC这些代称。“奇怪的人”是沈大成在《萌芽》杂志专栏的名称,现在出版的三本小说集很大部分来自于这个小说栏目,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她写作的内核。
《小行星掉在下午》里在超大型地铁站藏身的墨鱼人,一开口说话就会喷出墨汁;单身汉们成为了社会中的“次级人”,需要经过申请、面试进入一个家庭沉浸式旁观体验婚姻和育儿生活……
《迷路员》里在星空剧场打瞌睡醒来却洞悉了宇宙奥义的人;早已废弃却始终与居民共生的小镇百货公司……这些读起来奇奇怪怪的故事和人,关注的其实是宇宙中的各种存在,在虚构世界里,她以专属的奇思妙想描写着当代都市的生活现状和心理困境。
她曾做过一个比喻,好比有两个纸盒,你是只猫,你跳入第二个纸盒就不在第一个里。“我在第二个纸盒里散步,在里面想象奇异事物,为不存在的它们赋形。”
作家苏童评价说:“有些看起来是荒诞的叙述,在现实当中却非常对称,她的风格在同代作家中非常鲜明,独树一帜,对现实和超越现实故事的处理时常让人惊讶。想象力放松、开阔,摸不到边。”而作家唐诺自称是“沈大成的读者”,“沈大成想象世界和我们真实世界纤巧但坚实可靠的联系——不是特定的哪一个人,而是‘类化’的一种人、一组人,有着某种共有的特殊状态,某种处境乃至于困境。这样一组人一组人不断加起来,便遥遥指向众生。”

关于沈大成的那些事——基本写短篇
她目前发表过的小说中最长的是《实习生》,共有一万四千字左右,短篇更符合她现有的工作状态,也更适合现代人的阅读节奏。在她看来,好的短篇小说就像她喜欢的作家特利·比松创作的科幻小说《熊发现了火》,在这个故事中,一群笨笨的熊,齐齐走出洞穴,手持火把,在高速公路边,在密林中,在人类的居住地附近,围坐着取暖,并不富于攻击性,并且——他们停止或者说改变了千万年的冬眠习俗。在作者所构造的氛围里,讲述了一个由生命改变自然史和文明史的奇迹故事。
“这是一篇很神奇的没有任何‘科学内核’的科幻小说,它有一个很丰富的解读方式,而每一个解读的人又都觉得妙趣横生。这大概是一个好的短篇的样子吧。”沈大成不希望自己的小说里只有情绪,而没有故事性,她希望故事可以被转述给别人听。但她也表示不写长篇小说是感觉自己还没有“技术”来做这件事:“一直在短篇里玩耍,我考虑过写的更长一些,如果要寻找新鲜感,可能是需要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大的容器。”

关于沈大成的那些事——工科生的写作样式
沈大成是个工科生,这一点在她的写作习惯上有所体现,她写作的时候,会做一个Excel表格,列出已经写好的小说篇名,列出各篇的关键词、人物、字数等等。她说自己很喜欢写原始人和流浪人,而在这个表格里,如果小说有女性主角,她会用“F”来表示,但她发现目前为止,有这个标志的小说篇目很少。
她很少写两性关系,她更想写的是人和其他事物间的关系,就如《沉默之石》写的是人看待历史,就如《宇宙奥义的男人》里,设定是一个人如果知道一个天启,但这个人和天启之间的力量是不对等的,他要如何用人类的语言来“翻译”。她所思考的是渺小与宏大之间,人与世界、宇宙的关系。
“我觉得人太渺小了,但也不是说,渺小的人就无法承接极其伟大、宏大的东西,这篇小说里的男人在得到启示后,他看宇宙的目光变了,他变成了一个更为纯粹、更具理想主义的人。”另一个原因,她在读亚瑟·克拉克的小说《2001:太空漫游》时,很为开头着迷,这本书里很大部分都在写猿猴,她就想到原来小说也可以不写人,所以就有了《漫步者》,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有四只脚的天桥,某一天它拔腿就跑,各个部门想办法追踪,看看它想干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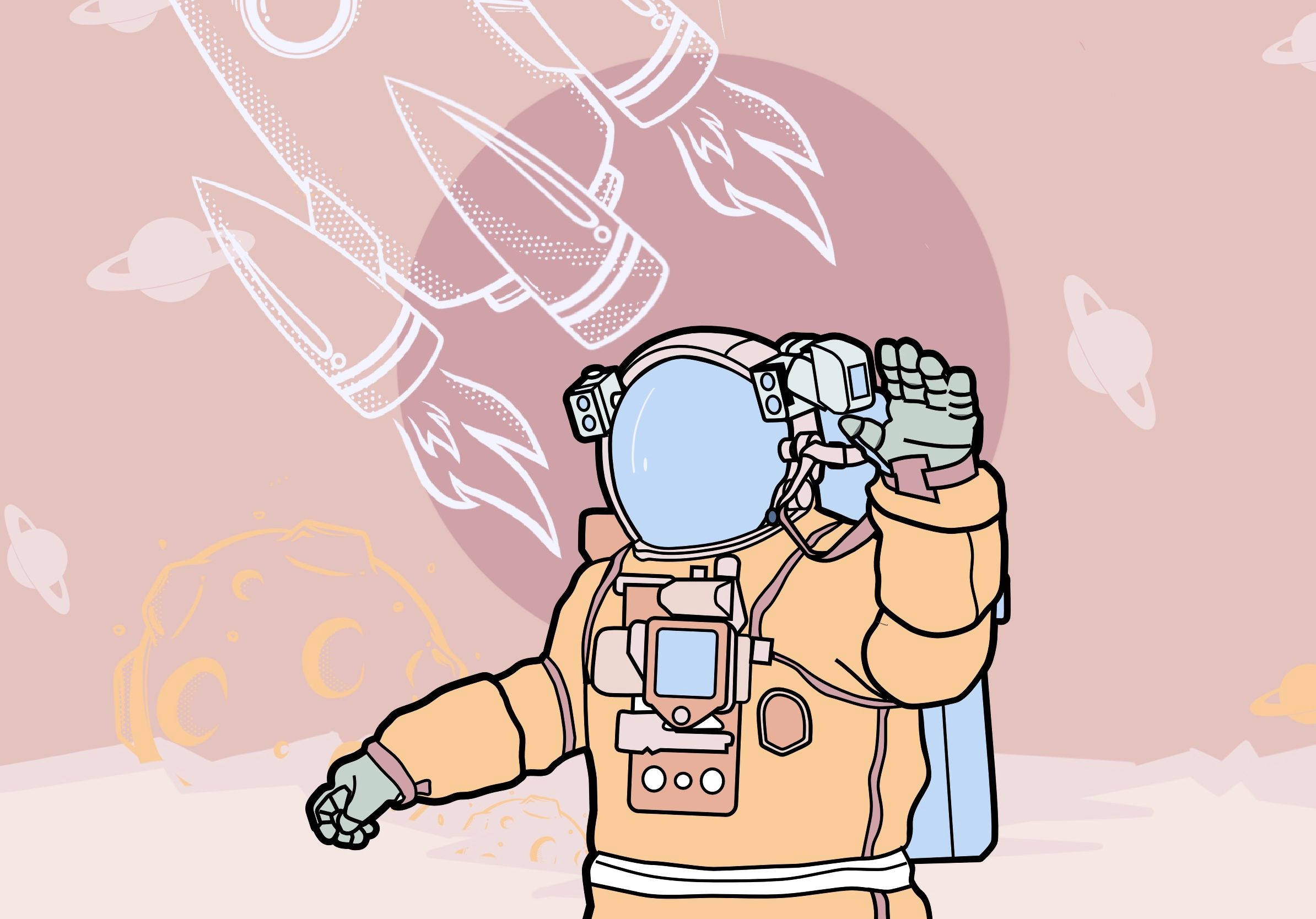
关于沈大成的那些事——小职员作家
广告公司文案——杂志编辑、记者——出版社文学编辑,几乎没有管过人,一直是个小职员。这是沈大成的职业轨迹,她从小就接受了父母一辈的观念:一个人天经地义就要上班,她还发现,上班有不少好处,给她发工资不说,上班还为她增添了社会属性,让她「更像一个人」。
小职员视线是在低处的,花大量时间精力处理具体的、重复的事,很容易体贴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很容易嘲讽高处的人,也许也会想象自己成为高处的人会怎么样——但是这最后一点沈大成总是想不下去。她每天想的都是几点乘地铁、几点去吃午饭这种事。她小说中的人和她自己差不多,她也觉得他们很亲切。
工作让害羞安静、有些“社恐”的她保持了和外界交流的窗口,接触到不同的人,生活经历也影响着她的写作。她回忆说,那家很小的广告公司,当时没有给每个人配电脑,她写文案打草稿是用圆珠笔在纸上反复写,通常一个礼拜不到就用完一支笔,写的差不多了再去一台公用电脑上打印。被称为“抠字眼抠得心灵的指甲都秃了”的文字,反而对她形成了一种锻炼。
在广告公司,她接触了配音、电影明星、大公司,它们在她的书里有所呈现。而她很喜欢现在所做的文学杂志编辑这份工作,可以接触到很多青年作家。“我很喜欢和他们的相处,甚至产生了一个滑稽的想法:误以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在看小说,但事实上,读小说的就那么一圈人。以前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同行都讨论比较现实的事情,而我总在想象一些奇怪的虚构故事,有时候不免产生一种羞耻感,但现在没了,因为身边的人都在做。”

关于沈大成的那些事——无处不在的想象力
《迷路员》中有一篇叫《星战值班员前传》,它说的是,星球大战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普通人并不知道,有一天,一个前半生很不成功的蓝领被叫去看一个仓库,人家告诉他,这个仓库里都是星球大战的物资,必要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动作,帮我们地球这方输送重要物资,他就一直在等这个时刻。
很喜欢搭建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故事,或者发明一种工作,因为生活中是很难无中生有的,你所有东西都是按照社会规范给你的条件去做,但是写作不是这样,你创造一个东西,无中生有。
有一天沈大成吃午饭的时候,想,自己现在坐在食堂里面,身边所有东西都是真实的,她就觉得,如果让她这个人完完全全地在真实中,她受不了。每天起床,上班之前在家里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一遍,然后就去重复地乘两条地铁线,上班,下班回来又要重复地乘两条地铁线,回家,吃饭,洗澡、洗东西、整理房间,睡觉……每天都在重复。而且不是原原本本地重复,而是在这种重复中,你发现自己做事情的速度变慢了,体力衰弱了,不能赶上这班地铁了……随着年龄增长在这种重复中下坠。
《花园单位》里的年轻人发现了人生真相:乏味的生活会真正地困住一个人。他就提醒自己小心,不要被掌管命运的力量看清自己是乏味的。这也是沈大成提醒自己的。写作就是她能找到的好的东西。她在茶余饭后想那些东西,你说有什么价值呢?没有价值,但是她需要思想存在于那些东西上,存在于一个假想的故事中。
每天醒来,她知道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故事在酝酿,在没有把它写出来之前,它仅仅陪伴着自己。今天一部分,明天一部分,这样持续性地生长,持续性地陪伴,直到把它写出来。她把想象一个一个如此编织起来,便是一次又一次非比寻常的旅程了。想象是路,是突围之路,而非一阵阵烟花。
想想看,自己何尝不是一个小职员主持人呢?但在岗位上各司其职,找到自己的平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绚烂啦。是不明显的烟花在心口的绚烂。
——小可
文本参考:《人物》——我最喜欢上班的部分,就是下班 作者:刘与、澎湃新闻《当小职员逃离日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