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遵义学者赵乃康——《且闿遗稿》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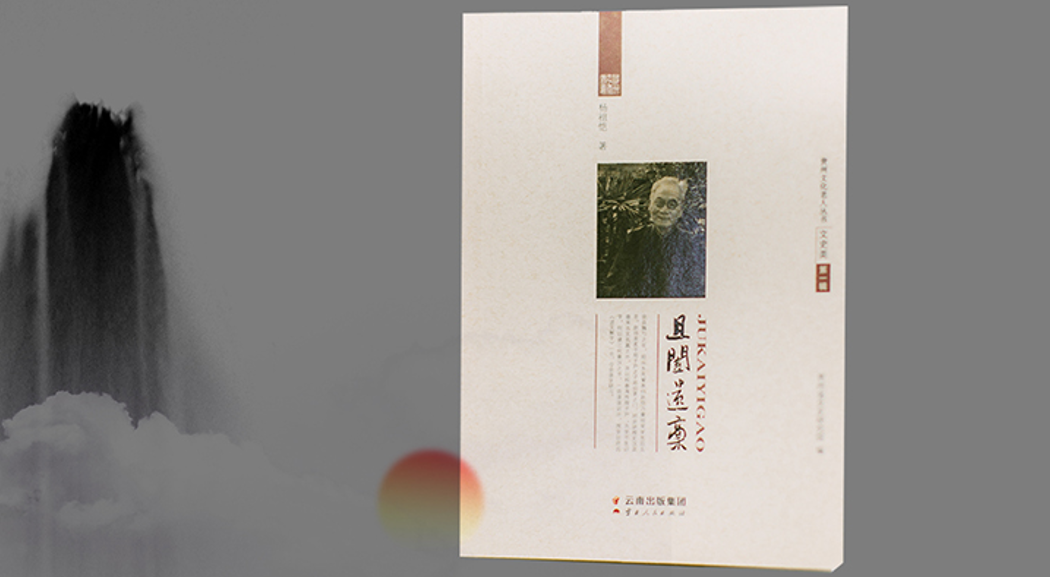
余自舞勺之年,即从乡先辈表伯赵恺乃康师受学先后五年。赵师亲炙于郑子尹之子郑伯更之门,对余讲授史汉及唐宋古文名篇之外,并以程春海传授子尹“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一语谆谆训示,授余以许氏《说文解字》一书,令余逐字研习。
——杨祖恺

遵义著名学者赵乃康,名恺,别号牂北生,晚号平叟,遵义县南乡团溪镇(清代属平水里)人。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卒于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享年七十三岁。赵氏为遵义望族,世代书香。先生伯祖父商龄字芝园,恩贡生。祖父锡龄字芷庭,副贡生,与郑子尹征君交契,郑赠诗有:
芝园终岁乐在渔,亦要芷庭能教书。
束竿放学携手去,笑砍芥姜同煮鱼。
又有为芷庭祝寿诗句称“相看俱老物,且喜各佳儿”。盖芷庭次子廷璜,又为征君之婿,生子三人,长怡,别号汉鳖生,进士,官知县;次懿,别号延江生,次恒,皆举人,均为先生堂兄。三人自幼承庭训,传郑子尹之学,并游宦家于成都。先生行七,幼亦受教于征君子知同之门,兼习举业,勤朴力学,入郡庠补恩贡生。因其长兄怡任成都客籍学堂讲席,遂往从学数年,更服膺征君学术。辛亥革命之后,长兄逝世,遗孤侄希道,荏弱少更事,先生力助其营葬。因长兄生前营一盐业,长期任人不善,至亏负颇多,先生回遵后,代兄家清理纷纭债务。以离乡久,情况隔膜,遇事多与先父葆辰公商酌。先父以表兄弟亲谊,悉力协助先生排难解纷,经历二三年,始得毕事。先生固笃于友谊,偿贷不足,不惜以已薄产作补偿,以绝后累。
先生家旧宅,原在遵义新城双剑山麓白沙井侧,与府学官署及文昌宫相接,人称文昌宫赵家。祖辈合居,生齿日繁,后即僦居邻近之陈姓房屋。此屋本系前清学官署院旧屋,地势高旷,庭院疏落。先生入居后,杂植四时花木于庭,庋文史书画于室,课余之暇,偃仰悠游,或则友明造访,学子问业,无不耳目一新,神怡心旷,咸称胸中丘壑,布置雅宜。
先生冲谦和气,平易近人,衣履朴素雅洁,绝少厉色疾言,在遵义中学执教前后近二十年,虽以讲授古文为主,无不以品端学赡敬重先生。先生又精研书法,大书擅小篆及北魏隶书,寻常笺札小字,则作苏体行草,求书者咸得满意。先生行文及诗,均本郑征君家法之传授。征君为文,受法于程春海,知同称为纯白古健,变化曲折;诗则初宗眉山,由韩孟以趋少陵。先生终身,拳拳于郑氏父子之家法,故其诗文风格,亦颇得其神似。
先生治学及教学宗旨,本郑氏学综汉宋为主,亦即阁百诗“六经宗许郑,百行法程朱”之义,教初学者从小学(即文字学)开始,以许氏《说文解字》为必读之书,然后“以字读经,以经读字”,循序渐进。至于义理之学,则重身体力行,以实事求是为主,不事空谈。先生读书勤奋,居室内图书环架,旁置竹几,翻检阅抄,倦则伏几假寐,醒又续读,有时终夜不卧,几成终身习惯。由于兄弟多人均承习郑氏之学,家藏巢经巢著作及各种版本亦最多。口诵心维,对郑学渊源端绪以及子午山故实遗闻等,津津乐道,聆听者咸为之神往。

郑征君子午山故居,其生前即毁于兵火。其子知同又南北饥驱在外,光绪中期,客死于广州广雅书局,子师惠扶榇返遵又道卒,由先生兄怡为料理,始送两丧归葬于望山堂废址。先生目睹心伤,无力挽救。后由川返遵,见知同儿辈,均贫困零落,所遗孤孀弱女,株守荒冢,生计艰难,时加赈恤。然当时子午山林木蓊蔚不下千株,其近邻豪狯,日夜明盗暗伐不绝,先生虽竭力呼吁保护,仍鲜实效。
后至民国十三四年,因重修火毁之禹门寺,遂尽砍子午山树木,只留征君母坟前二株。先生愤谓当时莫肯为言,官厅不之过问,从此大儒之墓,童濯一片。民国十八年后,政府有保护先贤坟墓之令,经先生建议创建郑莫祠,修建子午山墓庐,以及置守冢人家等措施,亦次第完成。
民国二十五年,省府民政厅厅长曹经沅以郑征君名垂西南,诗冠清代,明令定每年三月征君生日,地方官主持扫墓致祭,兼及莫黎两先贤。先生又计划再募集经费,次第修复子午山团湖、米楼等名胜景点,后因抗战开始,事未果行。先生又多方寻访,于四川嘉定找到知同惟一的孙子郑昌,接其回遵。清政府资助就学,并入浙江大学为旁听生,后任教于遵义以承名儒嗣,人尤称道。
郑征君生前无像,先生只及见知同及叔母郑氏姐弟等,证以知同撰《行述》所称“先子体貌端严,方颐广颡”等语,为工画者详为解述,相与商改而成征君画像以传。又复广收征君遗物,如子午山遗存木坊一件,先生以“禁橥”名之,实为一普通二尺许的木牌,内写禁折花木之句,正面为征君父雅泉书字,并有莫友芝、李蹇臣等数人跋语于各面。此物后归先生所藏,并详著录于《续遵志》中。足见先生拳拳于征君者,真无微不至。

遵义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州杨氏土司后,改土归流,设遵义军民府,仍属四川,自明入清,至雍正五年(1727年)始改隶贵州。前明知府孙敏政修《遵义军民府志》已失,经历百年后,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知府平翰聘郑子尹、莫友艺合纂《遵义府志》,梁启超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文中称:“郑子尹、莫友芝之《遵义府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
后民国三年,先伯父杨兆麟先生等倡议续修《遵义府志》,以草创初稿。后伯父去四川及广东数年,逝世广州,地方多故,志事中辍。
至民国十七年,周西成主黔,聘先生任总纂,县长乔运亨于老城曹兴蕲旧宅设府志局,先生约集各地学者整理初稿。数月后,先生送稿至贵阳,行时先父赠诗有“为君吩附东篱菊,元日归来始放华”之语。到筑后,省志局派司炳煃、杨覃生参同审订。司辞年衰未就,杨又牵连志事,先生暂留筑任教。与杨共审补府志稿,而先生致力为多。直至次年,黔军事变,周战亡,先生仓卒护初稿回遵,此后编审补校等,集于先生一身。延至1937年刊成,先生作四言体叙,有云:“本嫌虫技,未便蚁封,倘任斯弃,终恐飘飏……具此粗粝,敝帚自享。聊同绘素,敬俟贤良。”盖亦踵郑征君《遵义府志》之体例。

1939年,吴鼎昌时任贵州省主席,著名学者章士钊寄一诗于吴,名曰《访郑篇》,内有“西南两大儒,俱出牂牁巅。经巢尤笃实,纂述纷云烟……使君风雅伯,政化驰歌弦。盍往子午山,石口访遗编……”是希望吴能找到征君的逸稿,吴亦为显示政绩,方有捐资刊印《巢经巢全集》之决定。主其事者是省府秘书陈恒安,陈与先生均曾任贵州文献征辑馆编审,知先生平日收藏郑氏著作最丰富,函请协助。先生回函有云:“恺于经巢各书,搜求守残,转抄藏护已数十年,今一旦得印而存之,传布天下,乐何如之……此固千载一时之钜事也……”
全集由先生提供底本外,并编订全书目录。计征君著作共十五种,其中五种,系其生前自刻,称望山堂刊本,由遵义就原木刻版印刷,其余各种,由文通书局排印;又附郑知同遗著五种,全书四十册。目录后,先生有《叙》,洋洋千余言。文中阐述征君学术之纯正与深湛,而其子知同,亦以经学与小学名家,多所发明,言论为征君所许,足以辉映先业,可与高邮王氏、长洲惠氏、常熟翁氏相比拟,洵为先生晚年称意之作。

先生在遵义中学任教职近廿年,爱护青年,因材施教。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过遵时,徐特立老人曾访先生,询问遵义私家藏书情况,并嘱协助保护,免致散失。初拟设图书馆,后未果行。闻先生呈徐之诗,有“军中忙无暇,急急救文化。维护文物功,当不在禹下”之语。迨抗日战争开始,各地机关学校内迁来遵,不少名流学者,或以耆宿造访,或以诗文唱和。如浙江大学丰子恺、王焕镳、缪钺教授等,驻军将领如郝梦龄、专员刘千俊等,均推尊先生。在往还中,先生仍以阐扬地方文化,致力保护子午山文化遗存为念,曾编印《郑莫黎三先生事实征辑》《子午山纪游册》等。老友中,尤多黔省耆旧,如印江严寅亮氏,与先生为子女姻谊,廖宝珉氏为其兄恒乡榜同年,张振纲、陈瑞麟同在遵义三中同事。廖氏晚年曾过访,住先生家,诗酒酬唱。惜先生于1942年谢世,时吴鼎昌曾致挽联:
学术继乡贤,与拙尊屈庐相接,独任仔肩,郡志续成资政教;
仪型留梓里,广洨长司农所传,以承嗣响,宏编刊布念勤劳。
余早承教于先生近十年,后与表兄宗典又同校执教亦较久。1981年遇表兄于贵阳,得知先生自订诗文集稿,系交丁道谦带去上海,已难踪寻,遗稿亦已不存。今所知者,多散见于各书刊,后余从陈恒安氏得复印书札廿余页,借留手泽,盖亦不胜感念之情。

杨祖恺(1915-2010),出生于贵州遵义 ,精于隶篆,省内名胜古迹均有墨迹存世。1980 年后参加地方史志编纂、古籍整理等工作,曾任贵州地方志编委会特约编纂、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等职,1985 年受聘省文史馆馆员。出版有诗词联文合集《将就斋杂稿 》,遗著有《且闿遗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