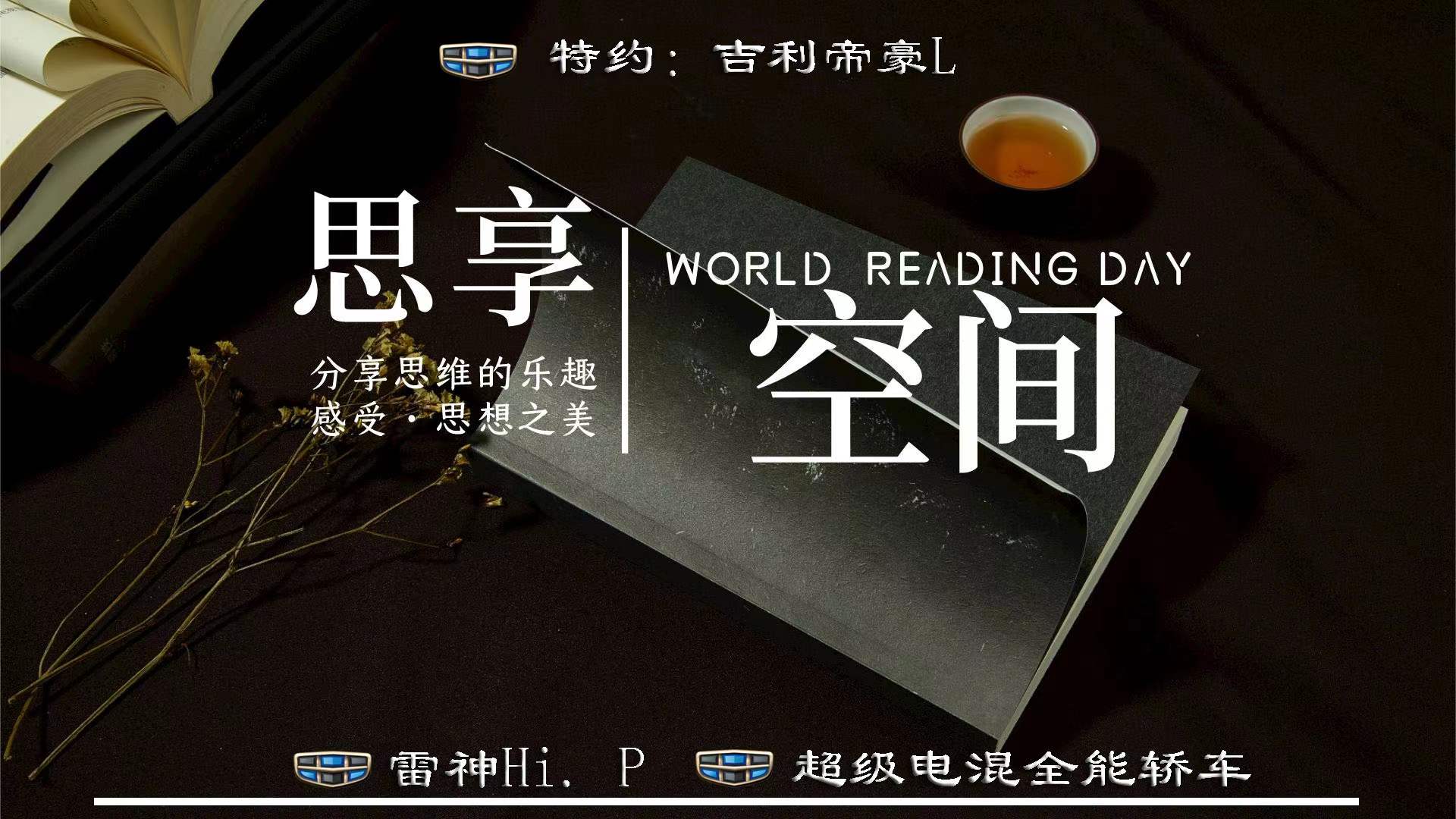思享空间·好书纪丨《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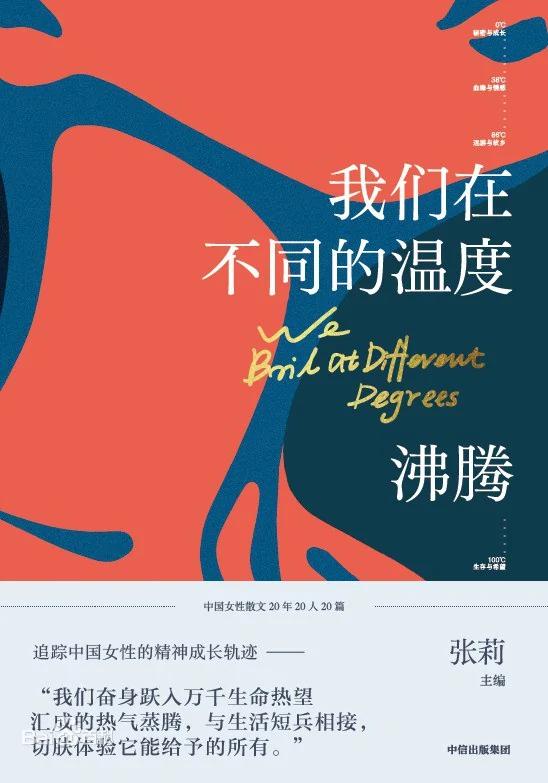
这是一本写给女性的书,从近20年的女性写作中,摘选了20位女作家的20篇散文故事。
翻开书,你会再次遇见那些熟悉的名字,周晓枫、李娟、杨本芬、毛尖、张天翼、张悦然、绿妖、林白、梁鸿……
在20篇故事里,有恐惧惊慌的少女面临成长,有颤颤巍巍的老妪互相牵挂,有女子体会切身的生育之痛,也有女子享受爱情的欢愉悲喜。
“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丰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张莉(主编)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不带伤
为了契合书名中的”不同温度”,张莉教授在主编这本书时,把20篇散文分为了四个主题,分别是“0℃秘密和成长”“38℃血缘与情感”“86℃远方和远游”以及“100℃生存和希望”。
0℃对应的是隐秘成长,这是女性写作中的重要主题,每个人都有隐密与伤痛,我们如何面对那些过往的创痛和羞耻,是以受害者身份“数伤痕”,还是以一种疏离的态度重新审视?
书的第一篇散文《即使雪落满舱》里,塞壬写下了一个女儿内心巨大的创痛,要怎么样面对父亲牢狱经历。
“太突然了,强烈的悲痛攫住我,我失声痛哭。突然间意识到,所有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的所谓尊严和面子,罪犯的女儿,这些都不重要了。此刻,我唯一需要的,是一个活着的父亲回来。”
直视伤痛,直视这样的事实。这位女儿选择读父亲从狱中写来的信,慢慢了解他,也原谅他。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酸葡萄,有的人会因此哭嚎,而有些人,则试图将酸葡萄酿成琼浆。
不控诉,不陷入受害者思维,努力从受害者身份中跳出来,以零度或最大的克制来讲述自身的伤痛,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美学追求。
这些作品引领读者直视女性生命中的创伤,既不沉湎也不躲闪,而是选择直面。
写出那一切——写出是倾诉,写出也是自省与自我疗愈。努力摆脱伤痕所带来的伤害,不被情绪或感伤所操控。要在疼痛面前重建一个人。

女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38℃的主题是血缘与情感,这一主题下,女性作家思索的是如何理解亲情、爱情、社会关系。
在脱不花的《相亲记》中,她把被动的相亲写得幽默欢脱:
“以失败开始,以失败结束,我的相亲记可谓是‘善始善终’‘始终如一’。不过,沮丧之余,乐趣更多,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识到了各色人等,千奇百怪地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也因此让我对人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充满敬畏。”
爱情或者婚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并不意味着全部。不恨嫁,也不被身边人的意愿裹挟,《相亲记》里的女性在清醒地做自己。
在爱情之外,亲情的羁绊同样深刻而复杂。在《对岸》中,孙莳麦写下了父亲离去对她的沉重打击,也写了她寻找新“支点”的茫然与慌乱,以及与母亲关系的变化。
“我开始意识到无论如何我的人生都需要一个支点。父亲去世后这种感觉变得尤为明显,从那以后,我清晰地感知到位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正在悄无声息地下陷。”
当年迈的杨本芬写下自己母亲的故事,当毛尖写下外婆对于包法利夫人的看法,当草白写下远去的祖母故事,当孙莳麦写下父亲离去时的疼痛……
这些亲人早已化作了我们生命中的滋养。这让人想到,女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的是写作者的社会性别意识,要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
张莉在序言中这样总结这一主题下的六篇文章:“真正的女性意识,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秩序,但又不被性别权力塑造。当我们被塑造时,每个人、每个女人也都有力量、有可能完成‘反塑造’。”

远方的意义是做自己
当沸点上升到86℃,主题定为了远游与故乡,远方对于任何一位写作者都是重要的,对于今天的女性散文写作尤其如此。
远方意味着与对远方之人、陌生之地的寻觅,意味着从熟悉之地移开,去寻找陌生的经验。那正是打开自我,重建自我的重要路径。
《我曾遇到这座城市的青春》中,绿妖写下了她离开故乡来到北京的经历。在北京,阅读、写作,饭局,唱歌,她找到了自己的朋友群落,也找到安心之所。
远在阿勒泰的李娟偶然遇到了苏乎拉。苏乎拉有许多让人费解的地方,也有许多可爱之处。李娟以清新而欢快之笔写下了一位新疆姑娘的传奇。
而林白,生命中的重要时刻则是从北京来到湖北,“一路上风雨兼程。心中只觉得山河浩荡,且波澜壮阔。”看到那些普通妇女,和她们聊天,从此,听到另一种市声、人声和嘈杂之声,开始创作另一种风格的代表作:《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北流》。
当然,去往陌生之地还包括对另一个未知领域的探索。一如冯秋子在《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所写,是现代舞唤醒了她。
“我感到美好,就走进去跳了,跳得有些忘我,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也是我的节奏和动作,我没有停下,身体在本能的自救运动中重新站立起来,接着跳。此时此刻,我在有我和无我之间,没有美丑,没有自信与否,只有投入的美丽。我一直跳,在一个时间突然停顿下来,因为我的心脏快找不着了。”
这也便是远方的意义、陌生经验的意义、自我敞开的意义——做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多么重要;遇到熟悉陌生而又深有能量的自己,多么美妙。

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
书的最后一部分,100℃的主题是生存与希望,《我们在不同的温度沸腾》中有着我们时代关于何为女性友谊,何为女性共同体的认知。
曾经是女工的诗人郑小琼,在《女工记》中辨认每一个与自己相关的“她”,她试图使“她”成为“她”,她努力叫出每一个女工的名字而不以地名或者工种指代,“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
“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淘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有着一个个具体的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
有新生就会有逝去,行超在《回家的路》中,写下的是农村女性的真挚友情。奶奶临死之前捎话让宏明妈去看她,而在她死后,宏明妈则赶来送别。老人在奶奶灵前沉默地叠着元宝:
“她们那样牵挂对方,也许就是对另一个自己的惦念。如同一生中的所有时刻那样,她们如此柔软又如此坚强,奶奶临走前缝好的最后一件小棉袄、宏明妈仍在不断折叠着的纸元宝,正是她们所能想到的、几乎是唯一的爱的方式。”
这样的讲述让人落泪,它以诚挚的笔触照亮了农村女性生活幽微隐蔽的一面,也还原了两位女性之间的一世情谊。而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女性友谊都比常人想象的要深厚与宽广。
这里所写下的每一位女性,都是作为主体出现的人,而不是沉默讷言的被启蒙者。看到她们,认出她们,写下她们,写下她们之间纯粹而真挚的情谊,是这些散文的共同特质,也是今天女性散文的重要美学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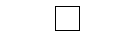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笔,写下她们的日常所见和所得,展现女性成长不易的过程,那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之光,力量在讲述中建立,这个时代的故事交由她们去讲。
——小可
文本参考:中信出版 《第一篇就看哭,这本写给女性的书,值得人人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