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声 · 悦读 | 她说,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关于敦煌的新闻画面,我们可能看过不少了,可是近日这一幕——当两位“敦煌女儿”92岁常沙娜和85岁樊锦诗在敦煌重聚,双手紧握站在一起时,好像没有比这更动人的画面了。她们约定“下次再来,保重”,令人触动。
分开为诗,两人各自为钟爱的事业倾尽青春与心血,合而为画,敦煌今时今日焕发新颜有她们的功勋。她们站定,给我们的是绵长的温暖,是令心静下来的仰望,更有取之无穷的能量。
惜别前,常沙娜俯在樊锦诗耳边说了一句,“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是啊,一生择一事,一世倾芳华,不就是动人的玫瑰人生吗?


01
常 沙 娜
已经92岁的常沙娜,
身上汇聚着许多标签:
“永远的敦煌少女”
“终身成就美术家”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女儿
人民大会堂建筑装饰设计师
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
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她最喜欢的话题总绕不开“敦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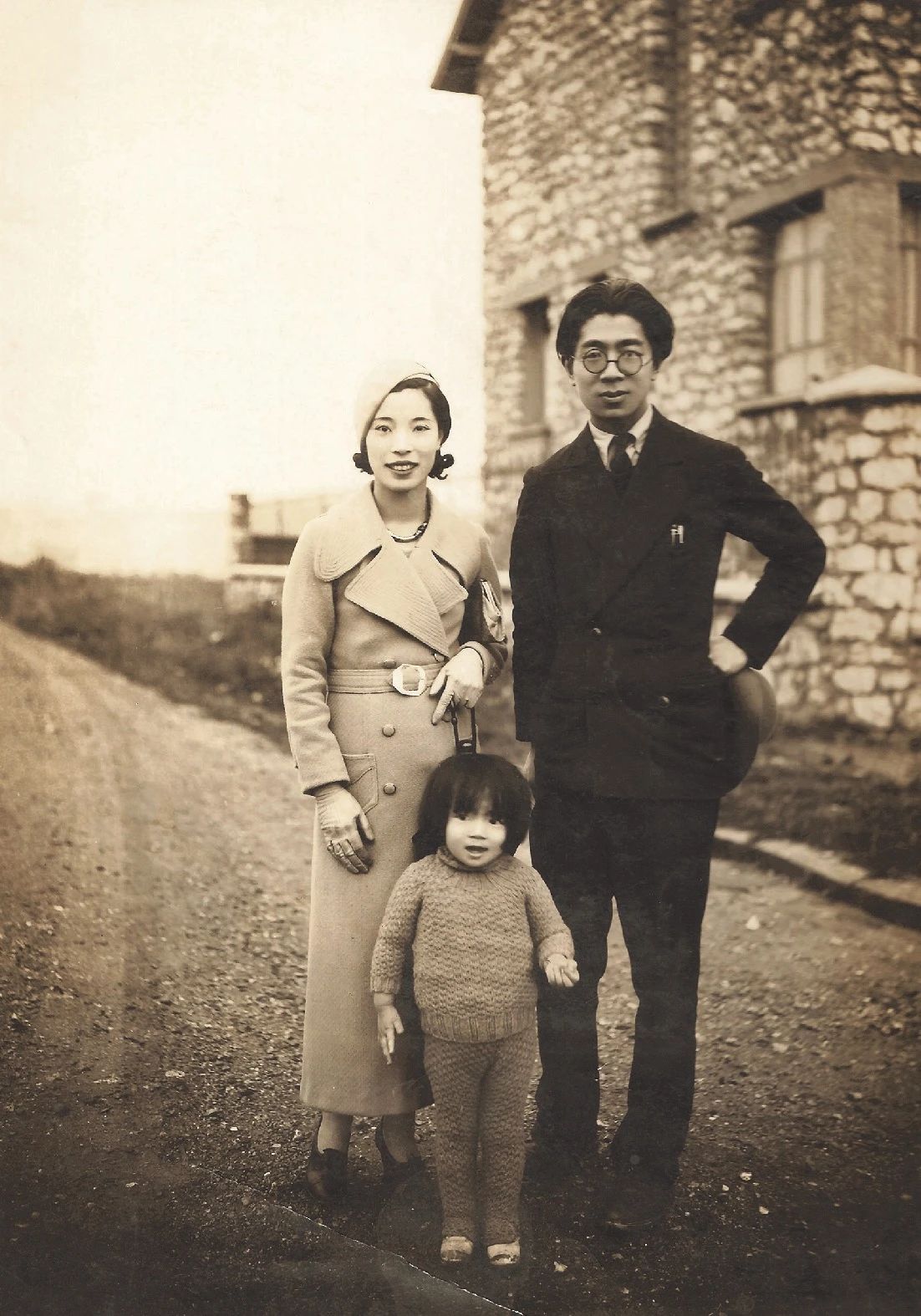 插图 | 常沙娜与父母
插图 | 常沙娜与父母
1931年,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
父亲常书鸿用当地的索恩河纪念她出生,
给她取了谐音的“沙娜”。
常沙娜说,“也巧了,
我爸爸后来一直在沙漠地带,
人家就说他的女儿早就叫‘沙娜’,
是沙漠里一朵婀娜多姿的花。”
她的父亲常书鸿,
就是后来备受赞誉的“敦煌守护神”,
曾有人预言,
只要常书鸿在巴黎待下去画下去,
一定会成为世界级的大画家。
可敦煌的召唤,令常书鸿
不顾成名在望、战火纷飞和妻离子散。
1944年,冒着连天的炮火,
常沙娜跟随父亲走进了茫茫沙漠,
走进了成为她一生牵绊的敦煌石窟。
他们第一顿饭用的筷子,
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
吃的是盐和醋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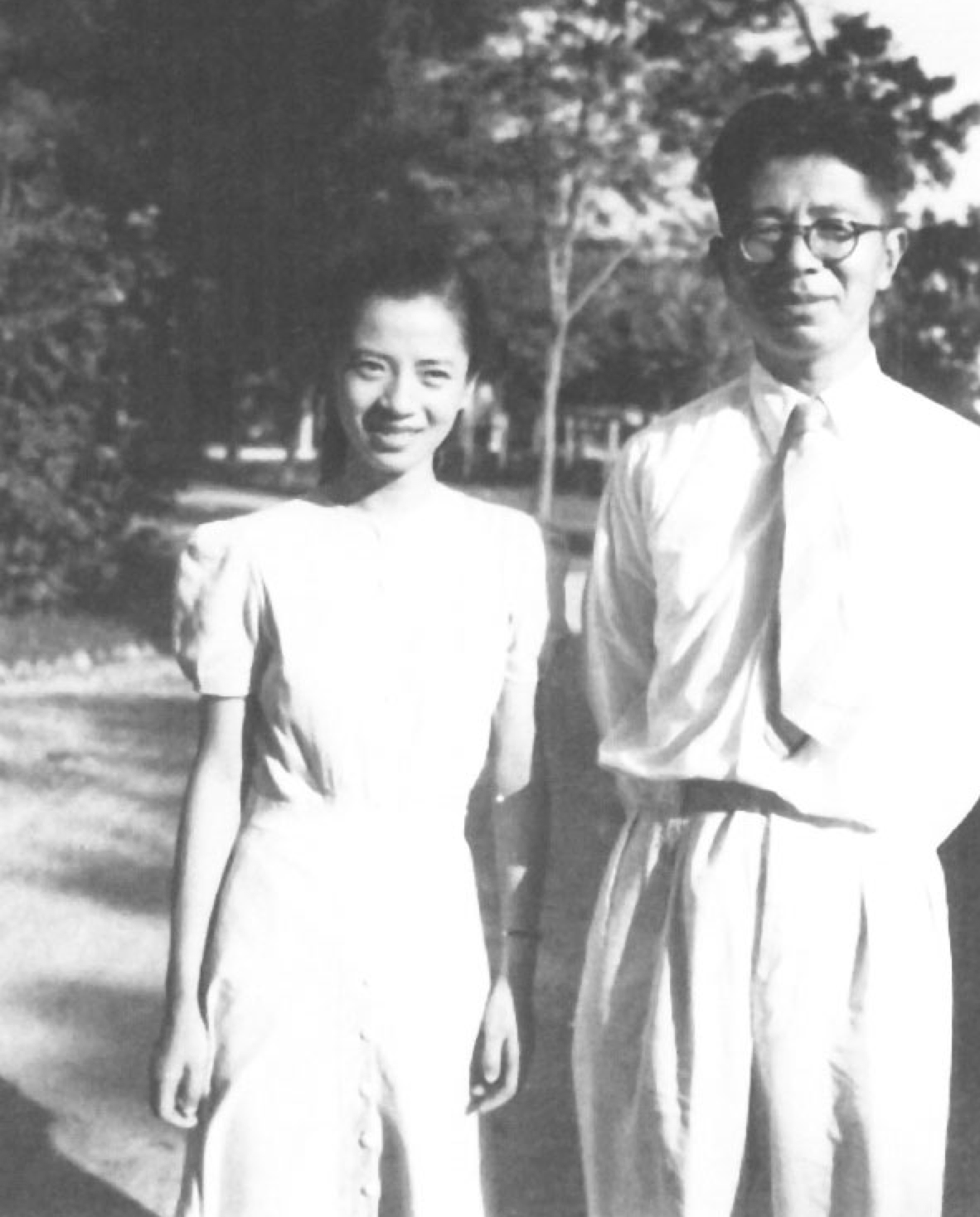 插图 | 常沙娜与父亲
插图 | 常沙娜与父亲
常沙娜曾问父亲“这么苦是为了什么”,
常书鸿泰然作答:
为的是保护好这些在荒烟无际戈壁滩上沉睡了千余年的瑰宝,不让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之辈,美国的华尔纳、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鄂登堡之流在莫高窟肆意掠夺的悲剧重演。
在父亲的感染下,
常沙娜便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
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她说,“我的基本功、童子功,
就是在敦煌形成的。”
建于五代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
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
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
吴道子般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
金碧辉煌如李思训般的用色……
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
她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


为宣传敦煌石窟保护研究的重要性,
常书鸿还举办了一场
以敦煌壁画临摹为内容的
“常书鸿父女画展”,
那时常沙娜不过15岁。
一次机缘,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对常沙娜非常赏识,
林徽因邀她来清华大学营建系协助,
自此常沙娜开始了工艺美术设计之路。
她身上流淌着敦煌艺术文脉,
敦煌图案的艺术精髓,
在结合了材质、功能的考虑后,
被常沙娜运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民族文化宫、首都机场
等知名建筑的装饰设计,
还有新中国第一块丝巾国礼、
纪念香港回归的大型雕塑
《永远盛开的紫荆花》。
 插图 |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照明设计
插图 |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照明设计

她一直没忘自己身归何处,
耳边时不时想起的是父亲的叮嘱: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了。”
她知道,自己一辈子,
都是敦煌的女儿。

时至今日,常沙娜在画册、在美术馆中
见到自己当年的临摹作品,
仍会“怦然心动”,她清晰记得,
那个场景美得像个梦,
画到兴致来了,就在洞窟中放开嗓子唱: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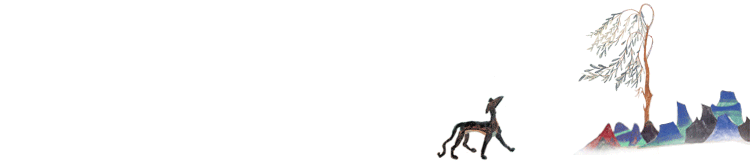
02
樊 锦 诗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在樊锦诗大学毕业实习时。
1962年,北大考古专业的樊锦诗,
被选中赴敦煌进行考古发掘。
 插图 | “实习生”樊锦诗(中)
插图 | “实习生”樊锦诗(中)
在她的想象中,敦煌文物研究所
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
可是一下车就傻眼了,
飞沙走石,黄沙漫天,
研究所当时的工作人员,
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
“一个个都跟当地的老乡似的”。
“实话实说,我当时并不想去敦煌。”
实习没结束,
这个严重水土不服的北京孩子,就撤了。
不过回京后,梦回千百遍的,
还是那一个连一个的洞窟,
以及洞窟里举世无双的壁画和造像。
毕业分配时,
樊锦诗又被“发配”去了敦煌。
父亲一度给校领导写信
陈述“小女自小体弱多病”等实际困难,
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去。
结果呢,这封信被樊锦诗一把火烧了。
 插图 | 1965年 樊锦诗与“异地恋男友”彭金章
插图 | 1965年 樊锦诗与“异地恋男友”彭金章
两年后两人结婚
火焰中,飞舞出
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飞天壁画,
就这样樊锦诗又回到了敦煌。
当时条件苦到,
习惯了孤独,
习惯了不怎么照镜子;
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
习惯了半夜老鼠掉在枕头上,
然后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继续睡觉……
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
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
确实是两个世界……
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
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
望着黑黢黢的窗外,
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
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
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既然“做梦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
她便甘作“敦煌的女儿”,
甘愿扎根大漠,甘心守护敦煌六十载。
她为敦煌所做的一切,
被季羡林先生称为“功德无量”。
就在今年7月,
樊锦诗又向敦煌研究院捐出1000万元,
鞠躬尽瘁至此。
常书鸿曾说,
他虽然不信教,但如果有来生,
还愿意做常书鸿,还愿意守护敦煌。
之于那些心归敦煌的人,
一生太短,热爱太长。
不擅长说情话的樊锦诗,
也把一生最美的“情话”给了敦煌:
“如果还有一次选择,
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03
一生择一事,一世倾芳华
在书写她们的过程,发现很多“人生之惑”似乎都有了解。她们站在那里,不用言语,自成答案。
如果你正因衰老而黯然,
看着她们,青丝落雪,温雅如玉,如果能像她们一样为所爱倾尽一生,就这样老去,不也挺好?
如果你正纠结,“走哪条路才不会后悔”,
看着她们,抉择时并不以“优渥”“安逸”“轻松”作为衡量标准,她们不都奔着心之所向去了吗?
心被安顿好,以后走的路就不叫流浪。因为指针向心,每一步都是“我心归处”,你会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踏实。

如果你正焦虑,静不下心来也坐不住,
看着她们,一路走来,若身后拖着的是一袭“患得患失”,何谈成事,何谈成大事。有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她们踏踏实实、诚诚恳恳地对待了手头的工作,对待了自己的芳华。樊锦诗有一句话叫:“当下就是涅槃”,问题是,你珍待每一个“当下”了吗?你一旦选定,就咬定不放了吗?
如果你正迷茫,关于人生还有很多疑问,
看着她们,“她们选择了敦煌作为自己的心灵归宿,敦煌也选中了她们向世人言说它的沧桑、瑰丽和永恒”。令敦煌充满魅力的,令世人为之痴迷神往的,不单在于那举世无双的文化艺术宝库,还在于痴守敦煌的人,所甘愿献上的一切。
最后,抛一个灵魂之问给你:
你愿意你的人生,借你的名字,向你的周围、向这个世界传递些什么呢?
希望你总有一天,无悔无愧地说出:“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内容 | 央视新闻《夜读》整编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