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岩叙 | 从煤棚到美食街,虎门巷藏着几代人随遇而安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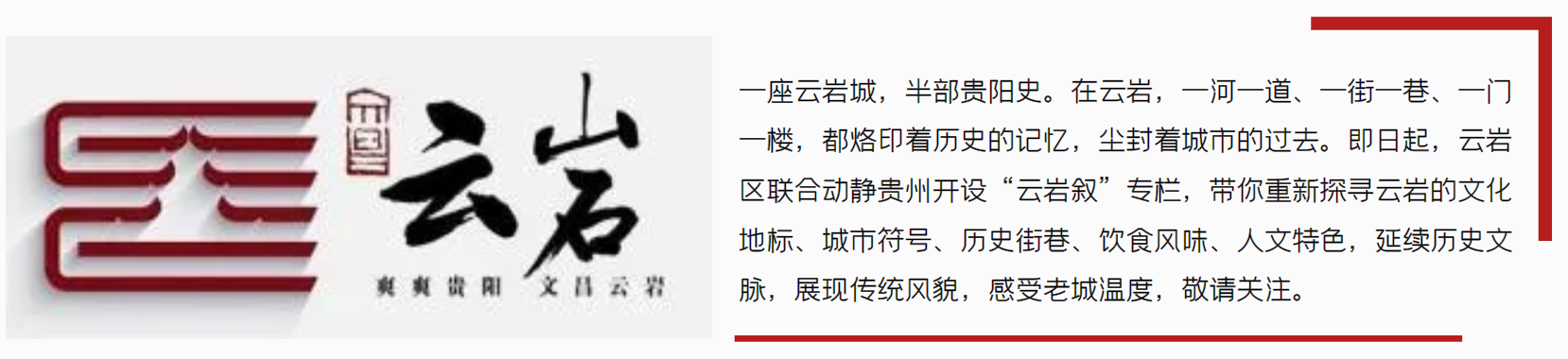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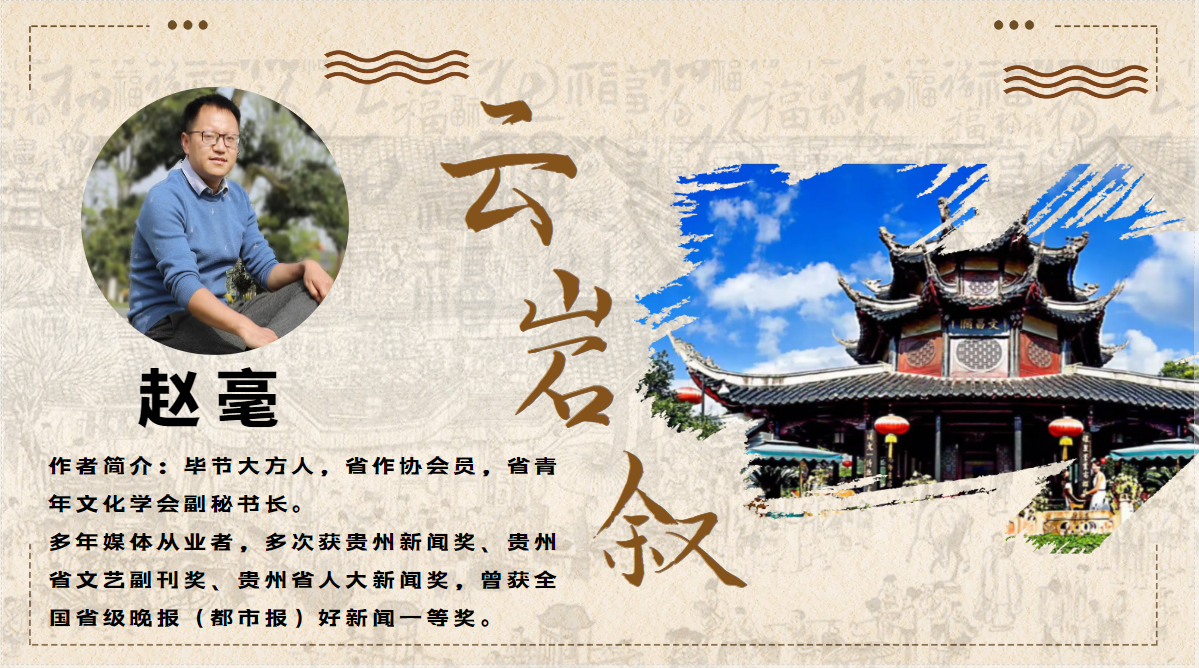
“我是一名佛系的店主”“不准打老板,再漂亮也不行”……在虎门巷逛一圈,许多小店贴出的标语,总让人忍俊不禁。这样诙谐轻松的调调,以及背后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就是此地吸引年轻人,从而成为网红之地的原因吗?或许随机询问几个人,都能得到肯定的回答。
 虎门巷陕西路入口
虎门巷陕西路入口
事实上,在网络流行语尚未盛行之前,这里早已人气火爆。虎门巷人气旺得溢满整条巷子,以至于两旁的居民楼,也开辟出了一间间别致的小店铺。通过和巷子里不同年代的人交流,慢慢回溯那些看似散乱毫无关联的故事时,想要的答案,也不由跃然纸上。
虎门巷中段的职人猪排,是大家口耳相传的名店之一。鲜有人知道的是,店主并非老贵阳人,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台湾人。据说店主多年前处于人生低谷时,应贵阳朋友之邀来散心。当乘坐18路公交在和平路站下车后,他无意间转入这条巷子,瞬间被眼前懒懒的景象所吸引,于是在此安定下来开店,后来他的店铺成为巷子里人气最旺的店面之一。
也许,大部分和他一样的店主,他们在某个时段迷茫、难过、失落,不经意间邂逅了虎门巷,发现了慢悠悠的小巷生活,重新找到自己,找到一种舒适的姿态,然后在这里安顿下来。
 深受欢迎的虎门巷老店
深受欢迎的虎门巷老店
普通又热闹的虎门巷,原来有那么多故事,有那么多人生的理想和梦,这是在飞速前行的时代,人们和市场的对抗,温柔又激烈。明白了这些,你就能发现虎门巷真正的魅力,感受到年轻人随遇而安的从容,是人生由此再出发的梦想,更是青年们活在当下,享受人间烟火的淡然。
令我惊诧的是,随遇而安的人生和理想,并不只是虎门巷做生意的老板们独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亦然。1936年出生的老工人郑绍义、1946年出生的大学教授吴宝琨、1958年出生的点酒店老板谢德敏,都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来到这里,然后一辈子扎根于此。他们同样活在当下、随遇而安,并不纠结于老巷子的过去,也不纠结于时代巨变和人生沉浮。
1961年,一句支援贵州建设,27岁的郑绍义和其他70余名国家统计局印刷厂的干部职工,便毅然南下,在一个接一个的山洞里穿梭,在期待、疑惑、惊奇里到了贵阳。他吃惊的是,从贵阳火车站出来,竟然都是黄泥巴路,房子普遍矮小,最新最高的建筑,是1959年开工建设、共9层不到40米高的邮电大楼。到市中心的中华路时,不仅路变得更窄,两边垛了灰浆的木制茅草房,最高的也才两三层,一点也不像省会城市中心区该有的样子。
无论是年近90的郑绍义,还是年近80的吴宝琨,他们记忆中的虎门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仅仅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变成了石板路。1980年代,木板房和茅草房拆掉了,才逐渐改建成了平房,巷子里的煤棚拆掉后,才由三步可以跨过,到可以通车。彼时,商品房成为中国的新兴事物,单位职工住房分配成为历史,购买商品房成为最新的时尚,郑绍义用工龄抵扣后,花9000多元,买到了总价10万建面50平方的商品房。当时月薪几百元,买一套房并不容易。
 活色生香的虎门巷深夜美食
活色生香的虎门巷深夜美食
199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下岗潮拉开序幕,许多下岗的虎门巷国有职工为了维持生计,因地制宜地利用门前的小煤棚,开起了洗烫店、烟酒店、精武馆、娱乐室等商铺,谢德敏就是其中一个。没想到的是,这些小商铺很快改变了虎门巷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家庭生活,并吸引了外地人到虎门巷发展。如今闻名遐迩的欣欣牛肉粉、289餐馆,就是下岗工人和进城务工者开的店铺。之后,类似的小商家越来越多,虎门巷也越来越热闹。
 夜晚的虎门巷
夜晚的虎门巷
时间进入新千年,随着煤气的全面普及,燃煤全面退出了城市,曾经家家必备的煤棚也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虎门巷所在的和平社区,在拆除了200余个煤棚后,腾出来的空间建了绿化。由于环境变化,许多商家和外地人到巷子租房子,职人猪排、代家干锅牛肉、川味刀削面、清水烫、高坎坎烤肉、安顺裹卷等纷纷入驻,虎门巷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期。与此同时,环境变好、治安加强、房屋增值,竞争也大了。
时代在变,虎门巷也更加繁华。2010年后,原记卤菜、羊肉粉、烧包、原始人烧烤、酒馆等商家先后入驻,巷子里的摊位和门面变得更多更挤。这时,商家们纷纷买房买车,原本狭窄的小巷出现了停车难的状况。作为第一个将煤棚改为烟酒店的人,谢德敏几十年来总是安静地坐在巷子里,看着这里从冷清到繁华,从贫穷到富足。她也曾经打算搬离过,但因为舍不得,最终留了下来。
或许,虎门巷的人都活在当下,并不关心过去。事实上,虎门巷的产生,和整个贵阳命运紧密相连:1939年2月4日,日本飞机轰炸贵阳,为疏散百姓,在新东门与洪边门间增辟一处虎门,老虎巷和虎门之间形成道路,遂名虎门巷。1944-1947年,为拓展市区范围,优化提升城区交通,依照贵州省政府第948次会议决定,撤除贵阳城墙,虎门消失,而虎门巷作为贵阳老街名一直沿用至今。
在细数虎门巷的历史时,我的思绪被拉到更久远的过去。数百年前,附近的红边门作为贵阳连接宋氏土司的码头,该是怎样一副人来人往的景象?彼时,匆匆忙忙的行人和客商,大概也无心思考过去与未来等问题,而只是在这里匆匆补充能量,然后开启新的旅程。无关过去与未来,只是享受当下的态度,不正好与今天虎门巷的人们一样吗?久远的文化基因总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谁能说今天虎门巷人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不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延续呢?
撰稿:赵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