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扶贫一线手记》总序
顾久
(作者系著名学者、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张兴老师将他的《大扶贫一线手记》三册相托,嘱我作序。翻阅三部厚厚的作品,感到这是由非常之人,于非常之际,所作的非常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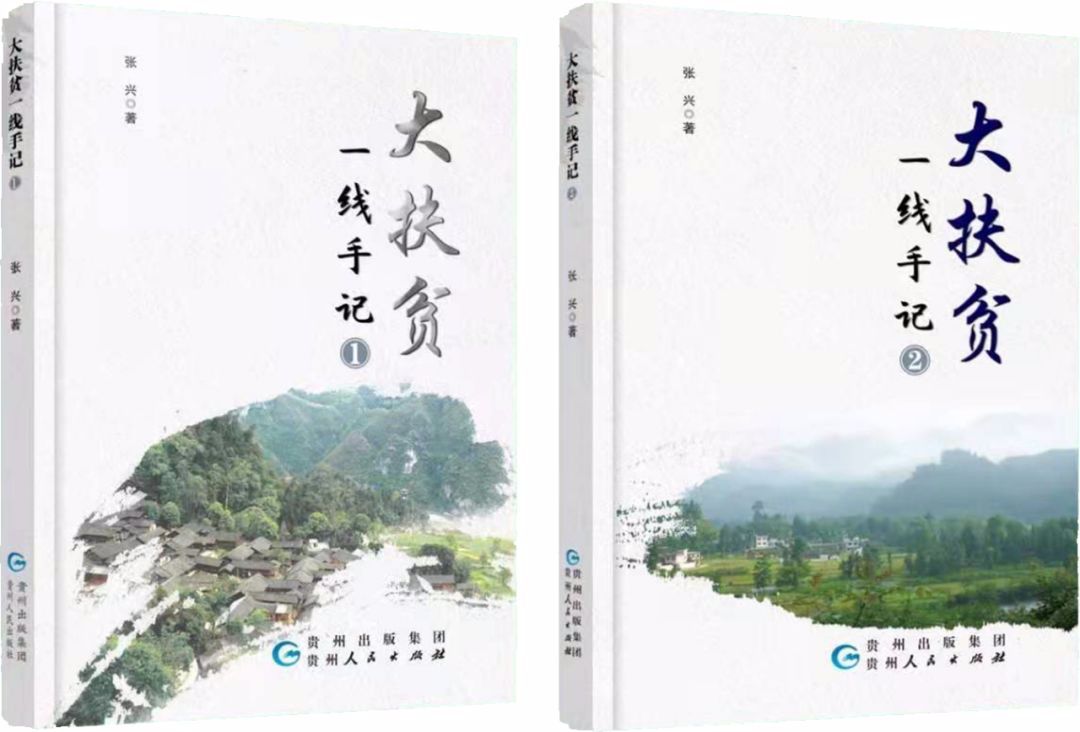
张兴老师属“非常之人”。其经历与我略同——从贵阳到黔东南凯里,因改革开放,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然后走上工作岗位——但我大学毕业后游移于好几个职业,张老师则一头扎根报社,从记者直到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曾斩获中国新闻二等奖、中国新闻奖副刊复赛一等奖、摄影复赛一等奖等,评为二级教授,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管专家等。其专业本为历史,却酷好文学,散文、诗歌等,出过几本专集。他身患严重的糖尿病,饭前必须打针,但退休后仍不息肩。脱贫攻坚战役打响,点燃这个衷情乡土、富于情怀、诗人气质和具有时代责任感的退休记者和永不下岗的作家的激情,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时得朋友邀请,或干脆自掏腰包,走村串寨于黔贵大地之上。共计五年时间,走访省内9个市、州和贵安新区的57个县市区,深入138个村寨,用尽3个手记本,满满书写了整整100篇纪实文学文章,编成《大扶贫:一线手记》三册。壮哉,张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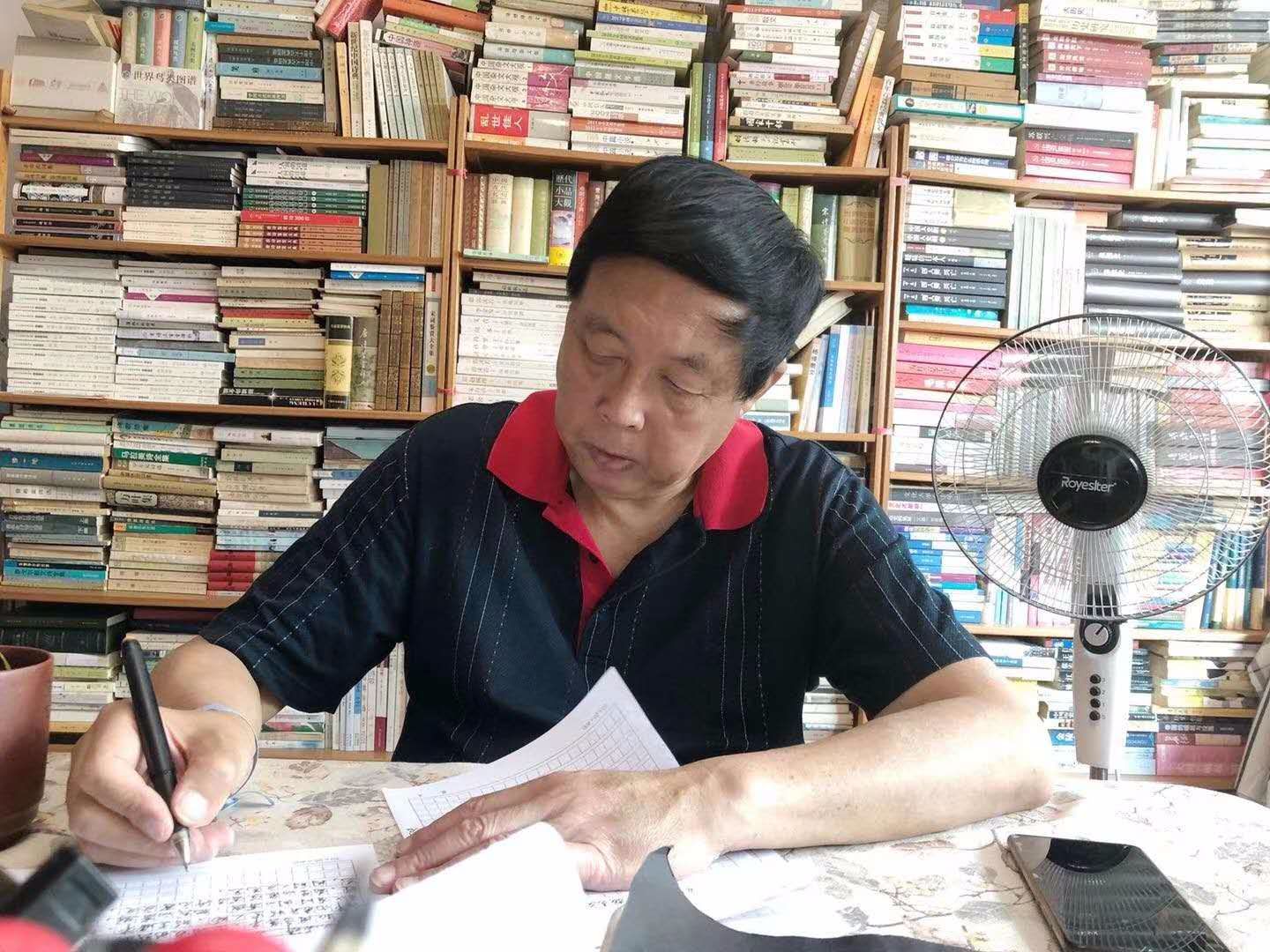
所谓“非常之际”,是说当我们这一代人步入晚年之际,中国三十年高速发展之后,又对贫困的农村进行帮扶。我们懂得什么叫贫困:1968年到凯里县一个苗寨上山下乡,我也曾摽着膀子与农民兄弟一道干遍种种农活。记得第一年干了286个劳动日,但至年终分红,除粮食而外,每天只分到1分钱——全年挣得两块八毛六分钱。那时,除买盐打煤油,所有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得靠自给自足。又过了十年,1978年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介绍,全省旱涝保收农田只有600多万亩,人均只有2分6厘田,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去年粮食社会占有量人均不足500斤,比全国人均少100多斤。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百分之三四十上社员的收入人均只有46元,是全国最低的。今年夏季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力只得2分钱……”而“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说得更直白。他这年去过贵州,说那里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他们当年长征经过的时候。”(韩钢.艰难的转型[J].中共党史研究,2011(09):21-28.)这就是当年的贫困。

贵州之贫,事出有因:这片土地十亿年前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还可能孕育过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但1亿多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引发巨大的褶皱;而约5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最终使这里形成青藏高原旁的第二台地。从此大山阻隔,河流切割,山深林密,人迹罕至。在狩猎采集阶段,这里的人类生存条件还不算差。进入农业文明后,山间土地破碎的农户,靠着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来维系生存,不可能不困窘。建省不久,明代人王圻对贵州的评价是:“古西南夷罗施鬼国地……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诈,……师旅绎骚,每与川、湖同其灾害,而军民岁计,又大半仰给于二省,兵荒交值,时有弗继之忧。”(《三才图会·贵州》)到了抗战时期,省主席吴鼎昌还这样评说:“黔省社会经济,尚未脱离中世纪简单之农业时代。予到任时,不但小规模之商工矿事业,颇少公司组织,即地方典当或高利贷等旧式金融组织,亦寥若晨星。除特货布匹药材等三五较大商业外,几无可令人注目之生意。汇兑不通,金融滞塞……合而构成之社会经济力量,其简单而微弱”。(《花溪闲笔》)
总之,“破碎的”、“山地的”、“小农业”,这三点几乎就决定了贵州的窘况。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对这块土地历来关心有加,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倾注的情与力更是空前。在此背景下,省委省政府用易地扶贫搬迁,来破解不适宜生存的“破碎的”土地上的村民;用改善基础设施——县县通高速后,实现村村通,再致力于组组通——来破解“山地的”阻隔问题;用特色农产品、合作社、企业加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的方法,来破解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加上种种社会保障来改善百姓生存——孩子读书、老人看病、通水通电;与此同时,动员万千各级干部入驻乡村,工作在第一线……贵州的物质与心态、自然与人文,都在发生着变化,日新月异,亘古未有。壮哉,时代!
贵州的这场巨变,需要类似《清明上河图》的画卷来展现其背景、事件、故事与人物……当然,场面更大,人物更多,气势更宏伟。凡有担当的文学创作者和新闻工作者,都不会失职缺位,于是,张老师挺身而出,从而成就了这部“非常之文”——《大扶贫一线手记》。
完成这轴大画,需要格局、文采与情愫。这些,张老师并不缺乏。原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总编辑宫喜祥曾评价张老师的格局:“远取诸物,近取自身;上接天文,下联地理;寓意深远,空谷余音;脚踏乌蒙,眼望星空;取材生活,立意人生;近观贵州,远望世界;聚焦细微,扫描宏伟;弘扬正气,鞭挞邪恶;速写自然,工笔生灵;胸怀民众,传播党性;言之有物,句句诤诤。”而原贵州省委政研室农改办主任、诗人赵雪峰曾赞美其文采与情愫:“张兴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尊重自己的生命。他用自己的诗,去写时代的苦痛。更用自己的诗,去关注人,关注人性,关注生命,关注命运,关注生命的意义,关注生命的存在环境,反映人在生命过程中的感怀、感受、感悟和感恩。他的诗歌细腻、粗犷、大气,有‘硬度’,也有‘柔度’,他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一路走来的脚步,一个人一路走来的难度,一种情一路走来的酸楚,他的诗歌值得让我脱帽致敬。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用水泥来勾缝的诗歌,又像是雄鹰在天空翱翔,点亮心灵,洞照精神。”



完成这轴大画,还需要独特的眼光和视角。从三部书看,张兴老师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开始,他似乎更关注记录大变革中的具体人和事:“我总在想,应该把这些故事都记录下来,因为它们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字里行间,都镌刻着我们不变的情怀与追求”,“这些人和事深深打动了我。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这样的人和事记录下来”(第一部《前言》);后来,他认为:“脱贫攻坚不仅仅是一项经济任务,而应该被视为中国农村的一项伟大社会变革。它所触动和改变的范围,应该涵盖农村的思想、经济、文化、社会、人文、环保、法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这一认识相适应,《大扶贫一线手记》第二部,把更多的视角和笔触对准了脱贫攻坚中的人文、社会变化”(第二部《前言》);到了第三部,张老师更把目光聚焦于人,并且是“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角度”去“关注人(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第一线扶贫干部和社会方方面面关注脱贫攻坚事业的个体和群体)在这场社会变革中的思想、精神、文化,乃至各种习惯、做派、作风的变化”(第三部《前言》)。于是,这100篇文章,区域涉及全省各地,人物涉及干部、农民、教师、企业家、反哺故土的爱心人士,等等。全书共有几十个农村干部和扶贫干部,“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少有豪言壮语,我更多地把落笔点放在他们不同的人生背景、工作方式、心理活动,甚至不同的人生命运上。只有一个目的:避免模式化、脸谱化写人,杜绝雷同”;而普通村民,“比干部多出好几倍。我写了他们积极的一面,但也不避讳他们消极的一面。本来,在这样一场历史性变革中,他们的不适应,有时多于适应”。可见,这100篇就像镜头对准了上百个不同身份、背景的生动人物。在本书的最后,张老师还附上他与人共同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愁》。壮哉,此书!

当年张择端在描绘《清明上河图》时,或许只是忠实于生活场景,精心勾画出眼前的汴梁清明节景色、建筑、人物、事件等,但却让我们感受和观察到千年前宋代的市井生活。张兴老师的《大扶贫一线手记》,是否也忠实记录了当下这个时代里贵州、乃至中国的历史变迁,从而让我们的后人也能感受、感慨和感动呢?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