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空间·叙谈录|编辑·摆渡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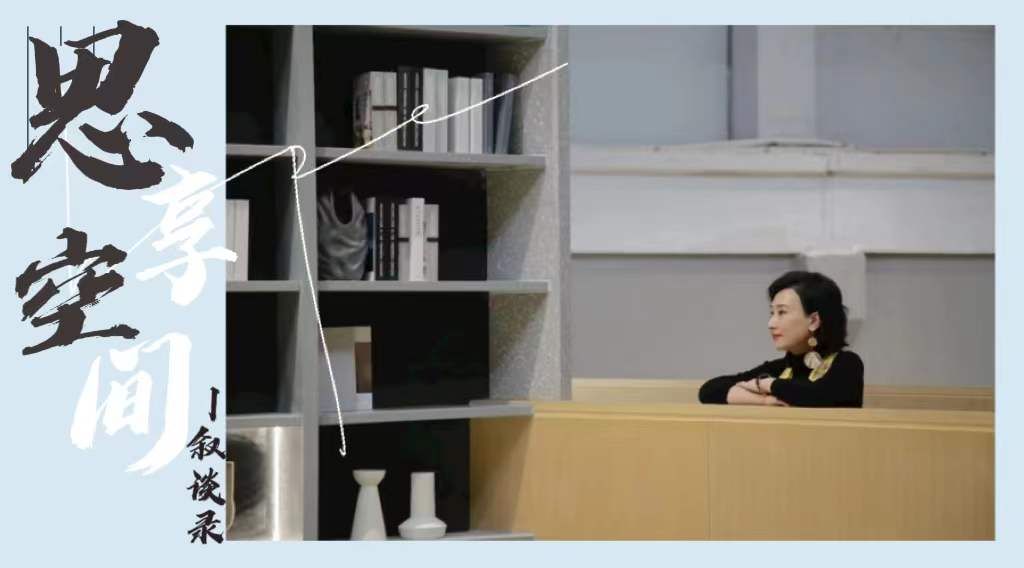
他是谁?
1、编辑——杨全强是一名编辑,如果你对人文社科感兴趣,你几乎一定读过他编的书,比如鲍勃·迪伦的《编年史》,《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或者在思想前沿的德勒兹、鲍德里亚。
2、出现又离开——他在出版行业做了22年,四次从零开始,辗转三家出版社,每次白手起家把一个品牌做出声响。然后,他就会离开,有时是主动,有时是被迫。但说起这些波澜,他毫无激愤,他只是朴素地讲述自己,不渲染和标榜什么。
3、出版是杨全强的庇护所,在相对纯粹的环境里,他保持着一种朴素的尊严。他做了很多原创作者的书和引进版的图书,至今看仍然「小众」。朋友揶揄他,是中国出版界的「赔钱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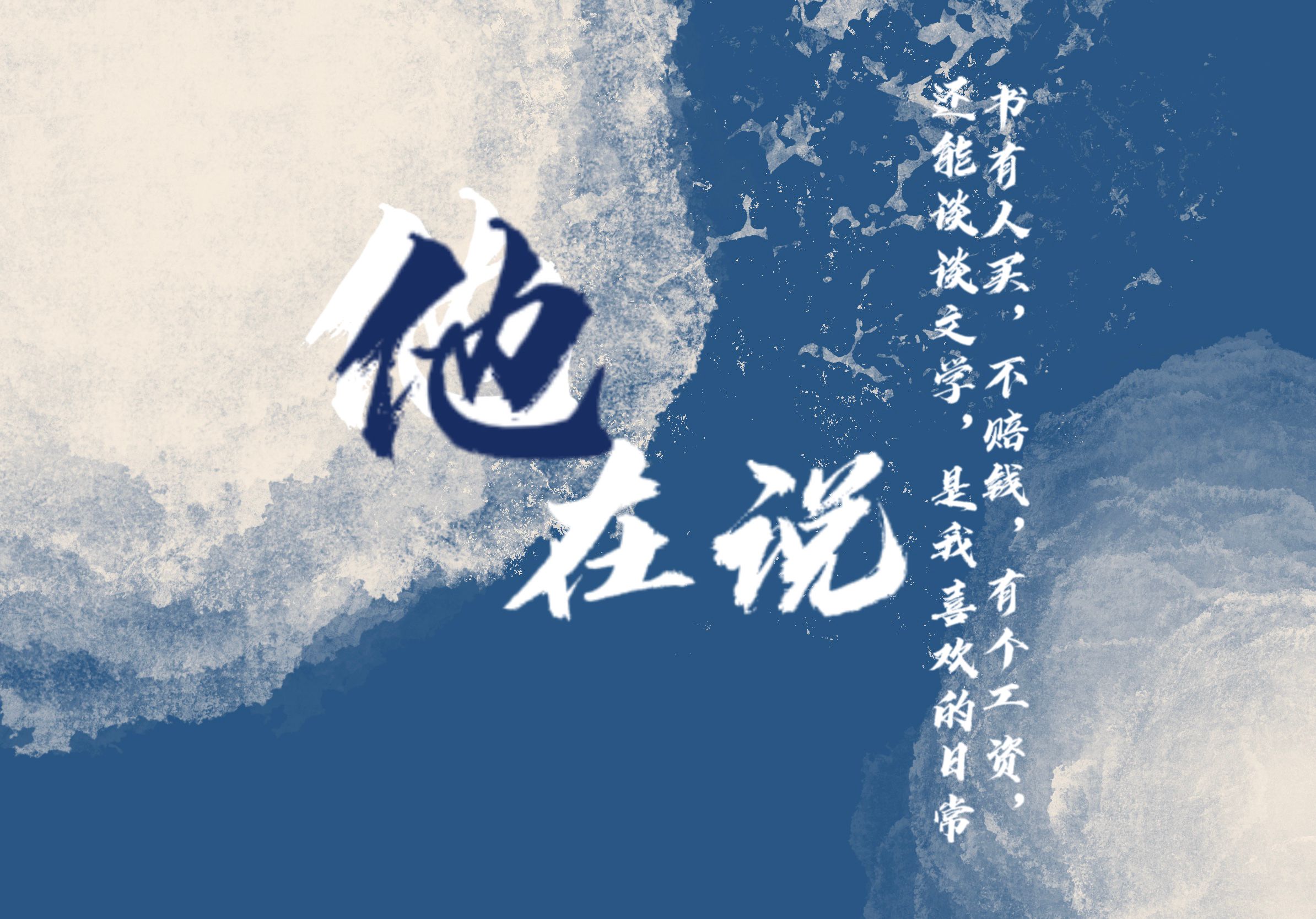
他在说:书有人买,不赔钱,有个工资,还能谈谈文学,是我喜欢的日常。
做书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平快的事情,一般来说五年的版权期,首印六千、八千,慢慢加印,就很好了。一本书可以这个月出,也可以下个月出,这种节奏感比较适合我。另外,做出版要和作者、译者打交道,喝个酒、吐个槽,这个行业,大家性格都比较散淡,书有人买,不赔钱,有个工资,也就够了,打交道比较轻松,还能谈谈文学,谈谈学术,是我喜欢的生活的具体日常。
我做的书里,最畅销的是《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鲍勃·迪伦的《编年史》也卖得很好, 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时做的《文化研究关键词》,今天还在重版,都快20年了。《刺猬的优雅》《南京人》《致D》《香奈儿的态度》都卖得还可以,也有很多卖了几千册。无论是作者还是书,都需要养,不像余华的《活着》,已经成为经典了,拍出重金把它抢过来就行。
但我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如果从销量衡量,我可能真的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出版人。但我也绝对不承认做的都是赔钱书,有些书你没看到,是小众的,但也不赔钱,我是有搭配的,在一家出版机构白手起家,有些书就要去铺垫,这些书就是炮灰,去填地下的地基部分。
有的出版社会紧跟当下的社会议题,比如一些很时髦的理论,女性主义,文明冲突,跟大家的社会生活感受更近一点;有的会去研究文征明(明代画家),看哲学家谈艺术,做一些类似萨特《什么是文学》、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这样的书。我是希望和当下的议题保持一点距离,再远一点,更形而上一点。我愿意去做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而不是更普及的《什么是女性主义》。
因为很多当下的问题,几年之后就不再存在了。曾经有一度大家都在谈论互联网,甚至还有人写过互联网史记。但几年之后,这不再是一个问题,互联网成为一种背景,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再过十年,女性主义还是不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有可能是,性别肯定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女性主义还会不会像今天大家争辩的这么激烈?我不确定。但是人的创造和人的审美,始终都是一个问题,它会有新的形态,新的体现方式,我关注的是这个。我试图在感兴趣的领域里做最源头的、公共性最强的书,既可以解释社会,又可以解释人的自我,也可以解释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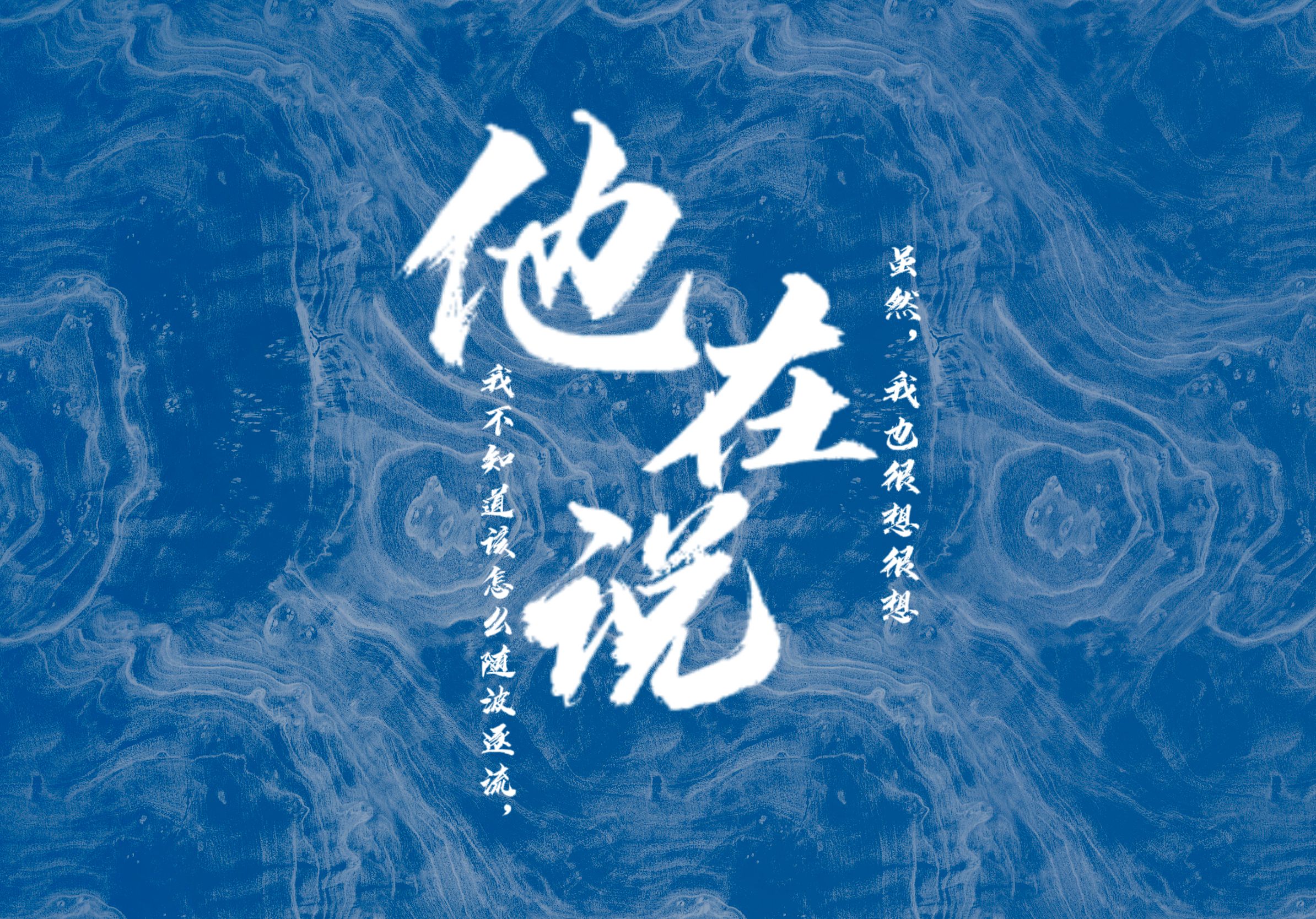
他在说:我不知道该怎么随波逐流,虽然,我也很想很想。
如果说有什么书对我的人生观有影响的,那还是《说唐》《说岳》和武侠小说。长期以来,我跟人交往,做一些事情,心里的标准都是李寻欢,还有乔峰,不自觉地会以他们怎么做来应对很多事情。李寻欢会帮助别人骗自己,当然没有人骗我,但我会觉得在有些事情上吃亏是没有关系的;乔峰就是性格豪爽,虽千万人吾往矣,很有英雄气概,不自觉地,也会影响我面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清高了,骄傲了,不能忍,就放弃,直到现在。
做出版,就是一些作品经过你,经过了就经过了。你也经过一些人,经过一些作品,但它不是你的。这都没什么,做出版没那么悲情。我已经很幸运了,还可以自主地让几百本书从我的手上做出来。我不愿意把自己放到一个需要被同情的或者要刻意去支持的位置上。
我出过很多作者的第一本书,比如倪湛舸、包慧怡、王敖的诗集,孟晖、蔡小容、汪民安,我做得也都比较早。克瑙夫出版社的戈特利布说,「我们应该成为某些才华出众之人的避风港湾」。我觉得出版机构应该是这样,你要允许有才华的作家出书,哪怕卖得少。
今天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卖得很多,能养活一个编辑,但他一开始都养不活自己。里尔克、卡夫卡都没有通过卖自己的书赚到钱。卡夫卡如果不去当小职员,里尔克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支持,都会很痛苦。他们面对出版商的时候,也很弱势。艺术是需要赞助、需要供养的。
出版就是跟创造的人打交道,跟那些能给人力量的东西打交道,但我们也不确定哪本书能给哪些人力量,那就首先让它出现。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选择什么,你去让什么事情发生,让什么东西出现,无非就是这些。我只是其中一个角色,没有随波逐流,因为随波逐流也不容易啊,你得知道它往哪里,能把你带到哪里,而且你还得跟得上。
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随波逐流,我也很想很想。

一首伟大的诗,真的抵得过一家大型企业。一家大型企业可能在某个时间段养活了很多人,但是一首伟大的诗,可以激励很多人,激励几百年的读者,都有可能。你今天去读杜甫,读他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你还是能获得力量;你读「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读「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就那么几句,1500年前的诗,仍然能给你一个刻骨铭心的瞬间,它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创造的力量。
——杨全强
文本参考:《人物》——我和“赔钱书”的漫长战事 作者:翟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