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与文化丨贵州北盘江流域的喇叭苗,为啥说的湖南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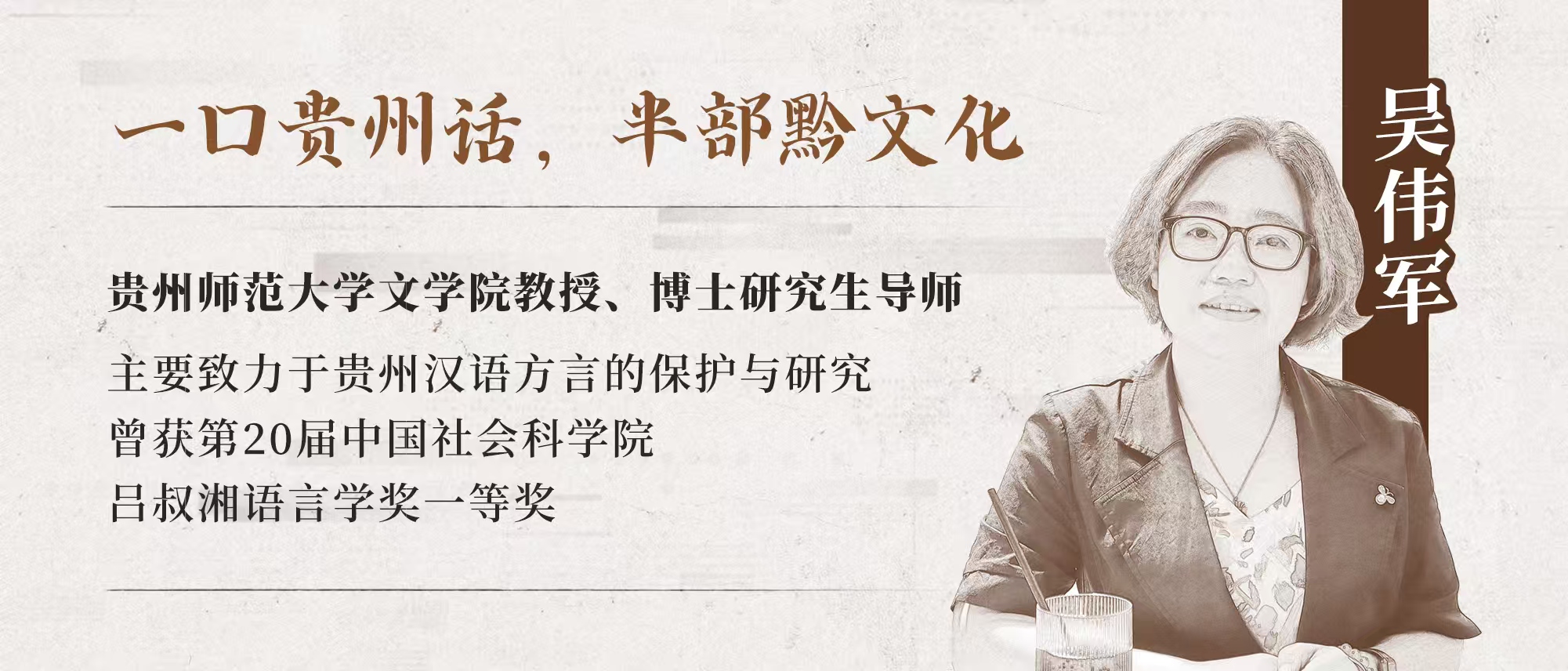
“点指点波罗,点到年家窝。年家吃酒,张家唱歌。大屋菢蛋,细屋送饭。送到哪底,送到瓦厂,打烂瓦缸。青布白布,水打葫芦,今年进财,明年大户。大点小点,小人蒙脸,蒙倒哪个,蒙倒各人脑袋角。”贵州北盘江流域的喇叭苗“土话”脍炙人口的童谣,在周边的居民听来却佶屈聱牙,十分费解。

北盘江流域居住着许多苗族支系,有四印苗、小花苗、长角苗、喇叭苗等。其中,喇叭苗的语言既不同于当地的苗语,也不同于周边的汉语方言,甚至彼此之间不能相互通话。同时,喇叭苗的语言内部还有显著差异,分“土话”和“客话”两种。“土话”属于老湘语,“客话”是带有湘语色彩的西南官话。喇叭苗与外界交流,一般使用“客话”。

成书于公元1008年的《广韵》中有10个全浊声母:“並、定、澄、群、从、崇、船、邪、禅、匣”。发展到元代,北方方言中一个都不剩,全部读成了清音。
喇叭苗“土话”则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这些古全浊声母,跟湖南新化、城步、武冈等地的方言有着较强的一致性。浊音是带音的辅音,发音时声带振动,清音发音时声带不振动。
因此,喇叭苗“土话”好多词听起来低沉雄浑。比如,童谣中的“葫芦”“菢蛋(孵蛋)”“送饭”“进财”“大户”等词中的“葫”“菢”“饭”“财”“大”“户”等都是浊音声母,听起来重浊低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喇叭苗“土话”保留了许多湘语特色词,例如,“孩子”“男孩”,喇叭苗“土话”称之为“崽”,女孩则称为“女崽”。说“徛”不说“站”,说“细”而很少说“小”,说“行路”不说“走路”,说“狭”不说“窄”,说“炙”不说“烤”,说“偋”不说“藏”,说“挟菜”不说“夹菜”或“拈菜”,说“禾”不说“稻子”。睡觉说成“睏觉”,闲逛说成“窜咍”,堂屋说成“祧屋”等等。当这些古书上词汇,在百姓口语中蹦出来时,我们会感受到方言的无穷魅力。

为什么喇叭苗属于苗族但却不会说苗语?会说汉语方言,但说的却是湖南话?这得从喇叭苗先祖的迁徙历史说起。《明太祖实录》记载:“初,官征云南,指挥使张麟统宝庆土军立栅江西坡屯守。至是,以其地炎瘴,乃徙于尾洒筑城,置卫守之。”这说明喇叭苗先祖系明洪武年间征南大军的一部。
明朝宝庆府所辖范围较广,包括今天邵阳、武冈、洞口、新化、新宁、城步、隆回等地。宋元时期,宝庆府境内多有苗族、瑶族聚居,但也有汉族,汉族多迁徙自江西吉安。因此,明代进驻北盘江流域的宝庆籍土军既有当地苗族和瑶族,也有当地汉民。

今天的喇叭苗“土话”总体属于老湘语,但却杂有赣语成分。由此推测,苗瑶族的土军在进入贵州之前已经跟当地的汉族充分融合,完成了语言替换。落籍贵州之后,由于戍守屯军的需要,这批土军又与当地苗族、仡佬族成家,经过数百年繁衍,逐渐形成特殊的族群。荆楚文化的遗风,在乡音中被一代代传承和创新。
附歌谣翻译:点将点将,点到年家窝。(到)年家喝酒,张家唱歌。大房(负责)照顾鸡孵蛋,幺房(负责)送饭。送到哪里,送到瓦厂,打坏瓦缸。青布白布,水打葫芦(瓢)。今年赚钱,明年(就成为)大户人家。(对打碎瓦缸的趋吉避难的解释。)点将点将,小人蒙着脸。蒙着哪个人,蒙到自己的脑袋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