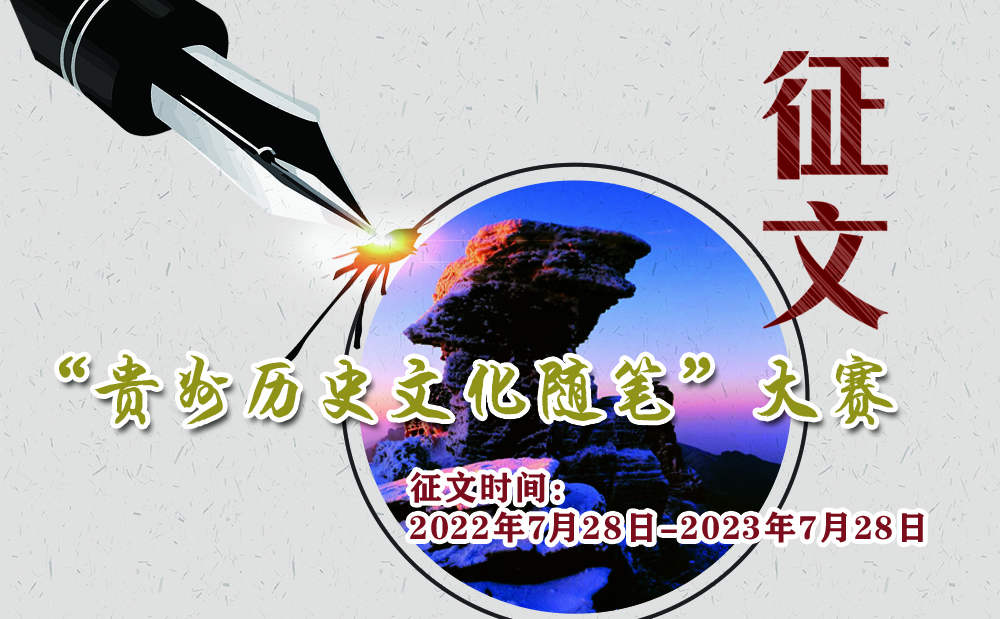【贵州历史文化随笔征文大赛作品选登】龙城走出张之洞
黔西南南盘江左岸的安龙县,因充当过风雨飘摇的南明小朝廷四年的皇城,而得此名,并誉为“龙城”。来到安龙,漫游招堤、十里荷塘、南明历史博物馆、兴义府试院遗址,拜谒明十八先生墓……在我不断为这里的秀美山川啧啧称奇,为这里的人杰地灵感叹唏嘘之时,脑海里总是跃动着一位历史先贤的影子。他就是从这里走出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张之洞。
 安龙招堤
安龙招堤
县城东北有座高大的石牌坊,上刻“招堤”二字。从这里可见三面翠峰环峙,一面紧傍城厢,一堤横亘其间。石堤西边是一波绿水,东边是十里荷塘,芰荷盛放飘香,曲桥倒影摇曳。沿脚下古老石堤向北走去,堤边垂柳依依,清风送爽。尽头那座小小的山头上,绿树丛托举着一座金碧辉煌的阁楼,颇像古塔。
山脚下有一招公堤记碑,记载着清康熙年间,兴义府游击招国遴倡议集资修堤,分隔湖水,结束了陂塘海子水患的史迹。碑后小山叫金星山,山上花木扶疏,掩映着历代修建的亭台楼阁,显得古朴幽雅。我想,这山上一定密布着张公少年时的足迹,亭阁内一定藏有他少年时的故事。
张公虽未出生于安龙,但他恰恰是从安龙这块土地上成长并走出去的。一条长长的脐带样的山路,把安龙与外界相连,也把张公与安龙这一母体连结起来。他四岁起便随父亲在安龙生活,从小喝的盘江水,吃的安龙粮,在这块土地上吮吸知识的乳汁,陶醉于清新的荷香,感受淳厚的乡情,体察民间的疾苦,从而扩展了他的文化视野,造就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苦读十余年,他从这山沟沟里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出了广阔前程: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并称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
金星山顶上那个阁楼叫涵虚阁,为三层六角三重飞檐造型,琉璃筒瓦盖顶,阁内迎面是一尊张之洞父子塑像。少年张之洞在伏案书写,父亲张锳站在背后,右手托腮,仔细端详,微露笑容。张之洞的成长其父亲对他影响很大。张锳为官30余载,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当年在安龙当知府时,经常在夜里派差役挑着桐油篓巡城,见有读书人挑灯夜读时,便将读书人的灯盏加满油,由此产生了一个常用词“加油”。
从涵虚阁东转而下,便是半山亭。半山亭坐西向东,因位于金星山的半山腰,西侧依附于涵虚阁东侧照壁墙面,使亭子呈半亭状态,故名半山亭,亭内镌刻着《半山亭记》。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兴义知府张锳所倡建的招堤半山亭竣工时,他在此大宴宾朋、著文纪事。其年仅11岁的爱子张之洞,即席作《半山亭记》,近800字一气吟成,震惊四座。“万山辐凑,一水环濴,雉堞云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翠,烟柳迷青,秋水澄空,虹桥倒影者,招堤也……”《半山亭记》文采洒脱,笔调秀逸,流畅练达,写尽招堤四时之景,文意绘景蕴政系民。文中竟有“德及则信孚,信孚则人和,人和则政多暇”的识见,有“与民同乐”的人本情怀。品读《半山亭记》,让人不能不感叹,他日后的成就绝非偶然!
下山来到山脚西侧的小广场上,在一片苍松翠柏簇拥中,一座高大的张之洞铸铜塑像巍然挺立。张公头着顶戴,身披官服,手握书卷,长须垂胸,目视前方,面容凝重,不觉让人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安龙金星山下张之洞雕像
安龙金星山下张之洞雕像
张公塑像后面是张之洞纪念馆,一幢面阔三楹的仿明清建筑。馆内有两块石刻引人注目,一块是毛泽东的题词:“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另一块是孙中山的题词:“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张之洞。”这是两位伟人对张公在引入西方科学、开辟中国工业革命中,所起作用给予的充分肯定和历史定位。馆中陈设集中反映了张公的生平纪事,其中,“张之洞法书”“张之洞百字文”“张之洞家书”“张之洞‘打虎’奏折”等分列四壁。他的书法笔力遒劲,自然丰润,俊迈豪放。一份“打虎”奏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兼署理两江总督时,在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八日(1895年8月27日)给皇帝的奏折:江西巡抚德馨利欲熏心,宴乐成癖,已经查明,报请问责。在他任巡抚、总督、军机大臣期间,多次上奏这样的折子给皇帝,充分体现出张公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和能言敢谏的性格。
张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清王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日趋衰败,气数将尽。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那个曾经威服四海的天朝上国,更变得满目疮痍,进入了社会变革的前夜。
回想当年,张公不愧是“救国精英”。他是“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个首领,他在武汉大办实业,拓展城市,大搞市政建设,促进了武汉的迅速崛起,让武汉成为中国内陆最大商业中心,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制造工业中心,揭开了近代化的序幕。因此,他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他创办的汉阳铁厂,是亚洲第一家集开矿、采煤、冶炼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是“东半球首屈一指的钢铁基地”,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因此,又他被称为“中国钢铁工业之父”。他提出并力主修建了1200多公里的芦汉铁路(后改名京汉铁路),成为我国腹地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干道,他又被称为“铁路主办元勋”。他反对沙俄侵略新疆,并起用冯子材,赢得了中法之战的镇南关大捷,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他一度支持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曾是他的座上宾,杨锐、杨深秀是他的弟子,谭嗣同、黄遵宪受过他的举荐奖掖。近来发现的史料《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证明,他还劝过慈禧速立宪政。当然,在他认清了康梁变法根本无法成功之后,便选择了明哲保身,立即和维新派撇清关系。对于这一点,也无可厚非,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古人。
1909年,张公这位清朝的最后柱臣,曾和摄政王载沣有过关于一项任命的谈话。张公认为“舆情不洽”,怕因此而“激出变故”。没想到载沣却毫不在乎地表示:“有兵在,不怕!”张公听此轻率之言大惊失色,认为当国者明知变故将起,却只想着以军队弹压,岂不是自绝于民,实乃亡国之言,当即口吐鲜血,病倒不起。张公辞世两年后,清朝覆亡。
当然,张公救不了信奉“有兵在,不怕”的晚清政权。客观上,他还为加速晚清灭亡助了一把力,有人把他称为“辛亥革命不自觉的酿造师”。张公用官费资送3000名湖广留日生,此中半数成为革命党骨干。他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也为革命党准备了充足的武器,也正是他仿德国兵制练成的“湖北新军”,打响了反对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所以“辛亥革命”又称为“湖北新军起义”。
作为政坛大腕之外,张公还是学界巨擘,中国现代教育的鼻祖。1898年,他在著名的《劝学篇》中,以完整的形态构筑了洋务运动的思想蓝图,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后演化成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之说,竟然同时得到帝、后两派的赞赏。他重西学办洋务,认为“非效西法图强无以保中国”,并成为他后半生几乎全部的心血和事业。他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讲道:“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他在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工艺学堂(今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等。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等。
张之洞堪称一代廉臣,不染于晚清腐败官场。在那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社会现实中,他这个总督居然成了当铺常客。因家中人口多,日子过得艰难,窘时“夫人典衣为置酒”。他谢世后的葬礼靠朝廷赏银、门人同僚奠仪才得以顺利举行。总督每年的薪俸一万多两银子,在当时是高收入了,但他的开支也大。他的幕僚是自己出钱养;各地发生灾荒,他捐钱;他曾捐款,在安龙建了一座小学堂;他还捐出慈禧赏银5000两,廉俸1.2万两在老家南皮办新式学校,题名为慈恩学堂(今南皮县第一中学前身)……他出任两广总督时,依例可得太平关、海关等处馈银20万两,这并非贿赂,而是惯例。他问明缘由,然后悉数充公,分文不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出任督办商务大臣再署两江总督时,一位道员为某富商私献白银20万两给他祝寿,借机请求在海州开矿。他闻之大怒,断然拒绝了富商的寿礼和要求,并弹劾罢免了这位道员。张公在遗嘱中称自己:“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在中国历代官场上,像张公这样的清官,该是多么的稀缺与难得!
在我即将离开这里时,我又一次站在张公塑像前,向他投去崇敬的目光。历史充分证明,无论古今,改革始终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张之洞关怀民生、关注国家的富强和发展,尽力助推历史车轮前进。他是清末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
作者介绍:

孙喜伦,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安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散文等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散文选刊》《绿叶》《北方文学》《岁月》《北极光》《中国环境报》《黑龙江日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集《寻梦之旅》《触摸沧桑》《蒙尘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