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藏着一所“中国的哥伦比亚大学”!|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贵州抗战印记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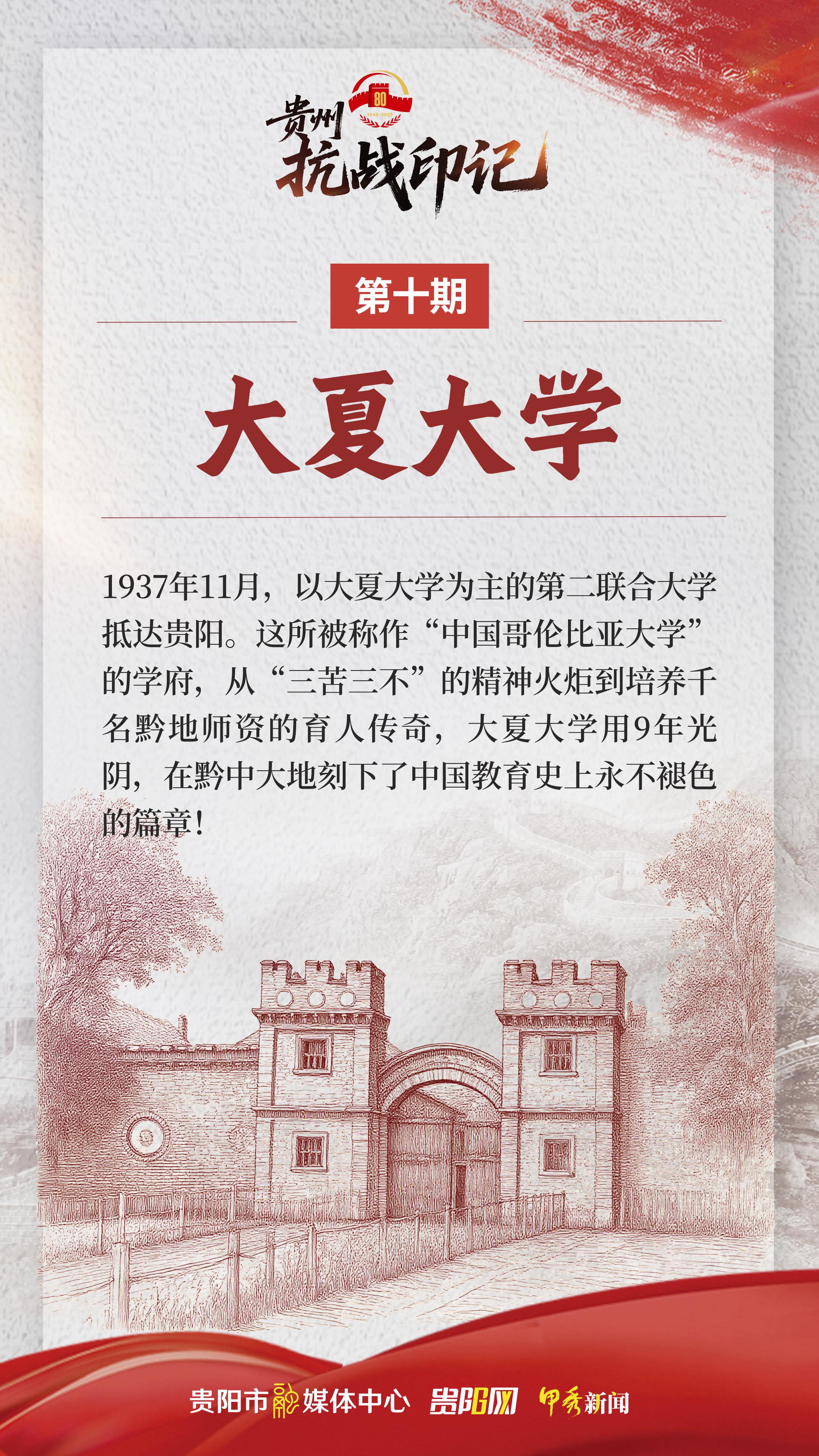
1937年11月,以大夏大学为主的第二联合大学抵达贵阳。这所被称作“中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府,从“三苦三不”的精神火炬到培养千名黔地师资的育人传奇,大夏大学用9年光阴,在黔中大地刻下了中国教育史上永不褪色的篇章!
何为大夏大学?
大夏大学是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24年,校址在上海,起源于厦门大学。
1923年,厦门大学部分师生与学校发生冲突,因而愤然离开学校到上海另建新校,这一举动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交通部长、贵州兴义人王伯群的支持。王伯群捐出银币2000元作为新学校的开办费用,遂成立以王伯群为董事长、吴稚晖等人为董事的校董事会,并任命马君武为校长、欧元怀为副校长。
学校最终命名为“大夏大学”,此名称既体现了其由厦门大学演变而来的历史渊源,又蕴含了“光大华夏”的深远寓意。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大夏大学为避战火决定内迁。经与复旦大学商议,两校决定组成联合大学,一同迁往江西庐山。然而,南京沦陷后局势愈发危急,复旦大夏联合大学不得不再次迁移,其中复旦大学迁至重庆,大夏大学迁至贵阳,并分别命名为第一联合大学和第二联合大学。
1937年11月,以大夏大学师生为主体的第二联合大学抵达贵阳,以南明河畔的原讲武堂旧址作为临时校舍。但随后因经费、人事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两校经商议决定自1938年4月起分开办学,并各自恢复原校名。此后,复旦大学留在重庆北碚,大夏大学则继续留在贵阳。
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后,立即得到了时任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大力支持,将贵阳次南门外原讲武堂的房屋场地拨给大夏大学使用。
迁至筑城后,大夏大学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王伯群出任校长一职,欧元怀担任副校长,吴泽霖负责教务长工作。在学科设置上,大夏大学在筑城主要开设了文学院、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以及法学院等多个院系。同时,还设立了师范、教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班,以及文史、政治、社会研究室等特色部门,并出版了《新大夏》和《大夏周刊》等学术刊物。
在办学精神方面,迁至筑城的大夏大学继续秉承了在上海时期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三苦”“三不”的精神。其中,“三苦”指的是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工苦干;而“三不”则是指学不厌、教不倦、行不惑。
1938年初,学校开学了。
经过几个月的颠沛流离,大夏师生们终于可以安顿下来读书了。
然而开学不久,学校就面临着经费困难。因为是私立大学,学校经费一般由学费收入,在上海时,不足还可以抵押校产借款,在贵阳,这个办法就用不上。
到贵州后,报考学生大多是沦陷区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区贫困山区青年,他们的经济条件远非战前江浙、淞沪富庶地区可比。其次,大夏在贵州本地招收的学生逐渐增加,据统计,第一学期黔籍学生共192人,占全校学生70%以上,此后,黔籍学生人数逐年增加。由于贵州青年大多贫穷,王伯群出于家乡情感,对品学兼优而出身贫寒的学生不舍放弃。以1939年下学期为例,全校注册学生300多人,获得全额免费黔籍新旧学生40人,半额免费黔籍新旧学生36名。
不仅如此,大夏大学迁入贵阳,使得更多的贵州省内贫困青年能就近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在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学校依然坚持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及采取减低学杂费等措施。这样,学校在开学时收取的学费往往只够3个月支出。这时候王伯群的经济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了,但他仍然竭尽所能支持学校。
此外,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还建有中共地下支部,领导和推动了该校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6月,大夏大学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发动全校教职员工五百余人,组农村宣传队,分九队赴贵阳县各片区进行宣传,动员全体民众,参加抗战救亡工作。
1939年5月,全校师生开展了“肃清贵阳文盲”的运动。
1944年11月,日军入侵黔南。王伯群心急如焚,决定动员全校师生再迁赤水。
受战局波及,物价急剧攀升,大夏大学一度陷入困境。赤水县长周世万充分发挥自身影响力,积极号召社会各界慷慨解囊、予以赞助,助力大夏大学顺利渡过难关。彼时,赤水社会环境相对安定,校园内读书氛围浓郁,学校发展势头迅猛。刚迁至赤水时,学校仅有学生863人,而到1946年春迁回上海之前,学生人数已增至1797人。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大夏师生同赤水民众欢欣鼓舞,举行提灯火炬游行,欢庆胜利。1946年9月,大夏师生及公物安然回到上海。
大夏大学迁来贵州前,贵州没有一所高等院校,仅有7所中学,教育并不受当局重视。
随着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颇有建树,抵达贵阳后,他们一方面从事教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当地的社会事务,特别是教育活动。两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和傅启学均来自于大夏大学,尤其是欧元怀上任后即着手对贵州的教育进行改革,重建贵州教育体系。
大夏大学在迁入贵州省的高等学校当中,规模不是最大的,师资也不是最强的,但与其他学校比较,大夏却是“与贵州关系较深的”,大夏培养的黔籍学生在战后多数留在了贵州。
从1937到1946,大夏大学在黔九年,以讲武堂为起点,以赤水河为见证,将“中国的哥伦比亚大学”之名镌刻进贵州教育史。这里走出的不仅是银行家、工程师,更是一代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黔地学子;这里留下的不仅是速写本上的山水,更是“刚毅坚卓”的精神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