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山漫记∣《矩州风物——就像玫瑰长在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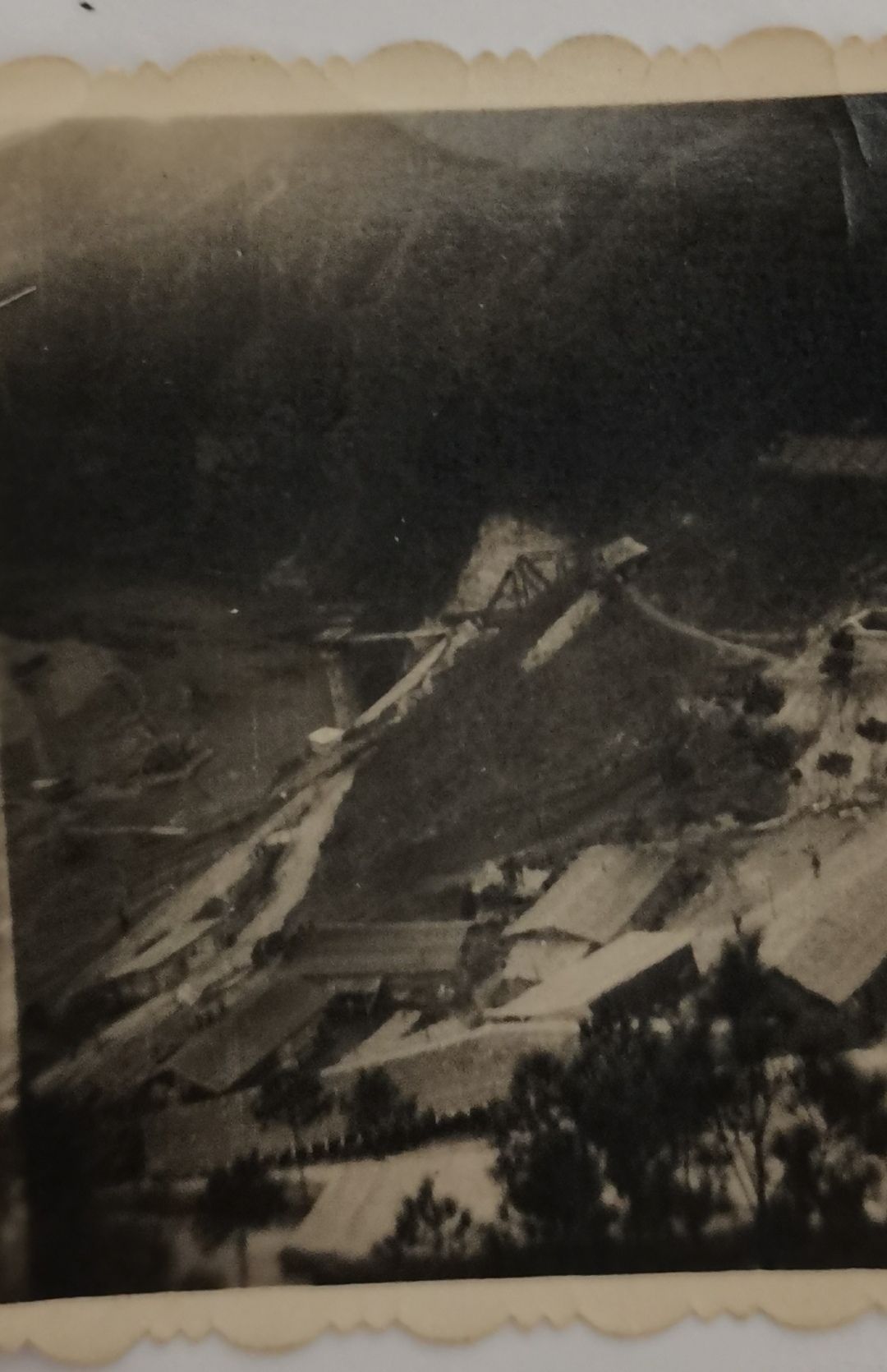
(该图片由本文作者涤之提供)
作者:涤之
一
1971年仲夏的一天,在成都八里庄中学读书的我,正虔诚地上着第一节课“早请示”;我那在成都理工大学教书的小姨母气喘兮兮地赶到学校,递给我一封电报:“得工作了。速回!母”
“我有工作啦?!”我不相信地喜出望外。小姨母拉拉我的衣袖:“别发呆了。快!还赶得上一个钟头后的火车。”顾不得其他,斜跨着姨父母、表弟每顿攒点,攒了快一年、晒干了的一大包那年月的黄金——红苕干,急匆匆地拜别姨父母,赶上了当天上午9:50的火车,一天一夜后的清晨,我回到了贵阳。脚还没沾地,亦还没将为什么问出口,母亲就压低嗓子亟亟道:
“别问了!等不得了!快!背上包,走!”母亲全身颤抖着、眼里含着泪、边说着边将一个捆好的棉被包裹挂上我双肩,不舍地随即将我搡给大哥,颤声道:“走!快!”
大哥手里捏着一本小书,轻脚轻手地拉开后门,拽着我的手出门就跑:“别问了,快跑!”
我被姨母、母亲、大哥一口气推到了离我家百米之遥的贵阳九中后门。惊魂未定的我,仍然还在墨者黑也的五里云中。大哥将我牵到大操场处一个戴眼镜、微胖的矮个子中年男人面前,轻声地给那中年男人说了两句什么话我没听清楚。那男人微笑着打量了我一眼:“上车吧!”
上车。什么车?前面几步就停着一辆有棚的大卡车。好几个学生模样的男、女生正在将自己的行李送上大卡车后车箱,然后自己也扒进车箱。
“我……也坐这个车?”
“别问了!快!上去。”
大哥驮着我屁股,把我推送进了车厢,又将他手中的那一本小书递给我:“不要再出来噢!记住了?千万!千万!!”
我疲惫极了,惆怅着欲言又止地看着车厢下面的大哥。
“记住,车开之前千万不要下车哈!”大哥不放心地已在叮咛……
车开了,我哽着喉头忍着的眼泪也掉了下来。我拿起大哥给我的书遮住泪眼,抵挡着同车席地而坐的十几双阴郁的眼睛。从我回到贵阳,再乘大卡车徐徐开出九中位于石岭街的大门还不到一个钟头,就像要逃离什么鬼魂似的,这下终于离开了,应该是安全了吧?可心里这么多的为什么搅扰着我,令我惴惴不安。忽然,“妹妹……妹妹……”是谁?肯定是叫我。这熟悉的声音,急促的呼唤。哦!是我大哥。我抬起头来,见大哥在大卡车从石岭街转纪念塔的弯道处,边跑着追上了大卡车,将一个小纸包扔给我,边对我挥着手喊:
“妹妹,自己多注意身体;到了马上就写信回来啊……”
我眼里溢满了泪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是挥着手,频频点头。大卡车越开越快,大哥的身影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最后,连小黑点都不见了。
家里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快速、神秘地送我出门?我得到的是什么工作?在哪里?我现在究竟去哪里呀?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校友柔声地对我说:“我们是去凯里修铁路。”咦?她怎么知道我的心声?修铁路?天……!我手无缚鸡之力,怎么抡大锤、打大石头?本就惶惑不安的我,又开始了更加胆颤的凄惶。
“我们都是去凯里修铁路的。这一车同学都是打前站的。”那女校友接着说。
“打前站?什么是打前站?”我不明白,问出了声。
“就是先去……哎!我也不是很清楚。总之,我们坐车先到,大部队走路后来。”
“走路?大部队?什么哦!”我低声喃喃。
“拉练。学习解放军。他们坐火车到杨柳街,然后走路到凯里,与我们汇合。”
为什么不坐车?还拉练?我越发不明白了,但没有再问。依偎着身边这位面容依稀熟悉、温柔平和名叫史娟娟的校友,随着车轮的滚滚向前,我还在漂浮着的魂魄渐渐落窝。
二
当天晚上9点过,大卡车将我们载到了一座大山里。黑咕隆咚的大山里静悄悄的,仿佛还有着轻声轻气的流水声。噢!一阵阵的风声与时断时续的虫鸣声、夹杂着大山的深邃阴森,令初次独处深山黑夜的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醒醒!李祥霓,醒醒!天亮了。”
昨天同车来的史娟娟叫我。我猛地醒了,睁开眼,呼!我们正好在山凹里。这时,迎面来了一位高高的男同学,不很友好地站在我俩面前:
“这是我们六连的驻地。你们是七连的还是八连的?”
还没等我俩回答,他手指着东方山腰:“左面是七连的地界,右面是八连的地界。”
东方山腰?我抬头往东方高处看,进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灌木丛,没有工棚,更没有房子呀!我感觉他是要撵我们走。突然,他看着史娟娟:
“你是史娟娟!我们一个院子的。我叫王黍强。”
史娟娟微微笑了笑。王黍强说:
“来,这是我们伙食团。来,进来。一会儿吃了早餐我带你们去山上。你们几连的?就你们俩打前站?”
“七连。”遇见熟人,史娟娟并没有怎样地高兴。
下午,来了几个年龄稍大些的男生,说是团部打前站的,来帮七连搭伙食团工棚。说着,他们就拿着堆在六连伙食团工棚空地前现成的木料、篾席,叮叮咚咚地开始干了起来。等我们在六连伙食团吃完中饭,七连的伙食团两间粗坯就已经搭建好了。哈!居然还有窗户。真好!阳光透过工棚射进来筛子眼一样的若干孔亮光,照亮了工棚内凹凸不平的地面,以及好些高高矮矮、长长短短的新花草旧枝蔓。我知道我们的“打前站”是什么工作了。不用谁指挥,我俩在七连刚刚搭建起的伙食团工棚内,将需要剪除的杂草、小石块除掉后就开始了我俩第一次的凿平地面工作。两天,我俩凿平了大约60平米的一大一小两间工棚地面。第三天中午,亦就是1971年7月6日的这天,七连的正主们走来了。
一百多号疲惫不堪的同学,渐次地走到了六连伙食团空地上,即刻就席地而坐下、躺倒。嘿!走在前面的不正是让我上车的中年男人吗?后来我知道了他是我们七连的连长,名叫钟必胜。
接下来的日子,七连的同学们从砍树、割茅草、搭工棚,凿平地、铺地板、架床板;起早贪黑地干了一个多星期,终于,我们七连140多号人结束了天当房、地做床、有了吃喝拉撒睡的地儿……
50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西南一隅的小城贵阳亦有了“高铁”;可“贵阳学生团二营七连到凯里50周年聚会”的29位战友,在当年的一排排长吕家成(吕大)、二班长赵成跃、安全员王应荣等同学的倡导、建议下,为了能重温当年乘上自己参与修建的湘黔铁路(凯里至贵定一段)第一次通车时坐老火车回贵阳的境况,硬是摒弃了从贵阳到凯里只需34分钟的“高铁”,全体乘坐要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凯里的“绿皮火车”。如此,这群50年前二营七连的青年战友,慢慢地一路唏嘘着自己从少年到白头的50年岁月、欢声笑语地“摇”往凯里。
真遗憾我没有与战友们一同乘坐绿皮火车去凯里,错失了战友们好多精彩的回顾。不过还好,我们仨(李祥霓、张晓云、杨瑞云)因为害怕迟到,亦乘坐上与大伙同一天且几乎同时出发的7月6日9:55高铁,在凯里“维也纳3好”宾馆前厅,殷切地等了3个多钟头,终于与二营七连的大部队汇合。呵呵!我居然能面对面地叫出了95%战友的名字。是命运使然还是性格决定?我竟然于无意中复制了50 年前比大部队先到三天、50年后依然比大部队早到3小时的宿命。
骄阳烈烈已午天。50年后的2021年7月6日下午三时许,七连的男、女战友们,最大的74岁,最小的66岁,共计33号人,终于来到了我们生活、工作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湾溪清水江畔。
山中一块平地上,突兀地出现了十多节破旧、被遗弃的、但橙黄色明快依旧的火车车厢,几步之遥处废弃的铁梗大桥、似是而非的“新插旗山隧道”,还有山脚下依然无语东流的清水江、江边的那块滩涂;按方位视觉,大家肯定此地就是50年前的学生团二营七连驻地。面对昔日镜像残存的在线(再现),引发了战友们的哀婉伫足、兴奋感叹,一个个看着彼此熟悉而陌生的脸,毫无顾忌地打开了尘封50年的湾溪往事,一桩桩、一件件地漫漫倒带:
“大桥,就是这座大桥。蒋学兰、黄润芝和我,我们几个在这座大桥上,想照张相片留念;可还没有照呢,就被几个民兵吼住,还收了我们的相机……那些人还到我们连来带走了我们仨。当了解我们是修铁路的学生后,曝光了我们的胶卷,还了我们相机,就放了我们……”
50年前娇小漂亮的战友文琳,如今漂亮依旧的摄影师文琳讲起她们仨当年在大桥上发生的故事,爽朗地呵呵直笑。
“……我们是坐车到‘三棵树’下,拉练(走路)的。我们在麻江、下司住了两夜,第三天到达湾溪的……”
在客车上,坐在我身旁的王应荣撸起裤脚,在脚踝处比划着:“在生产队的仓库里驻地那天,夜里被什么东西咬了,瘙痒难耐,睡不着觉,与向开建(亦是七连战友)到门外,借着月光一看:天哪!脚脖颈处一大圈密麻麻的小黑点在蠕动。你猜是什么?像一层黑芝麻(我摇摇头)。是一圈跳蚤。跳蚤密密麻麻地死咬着我的脚踝不放。向开建身上也有。我们俩将跳蚤一个一个地抠,抠了好大一歇才抠干净,可身上脚上被咬了的地方不抠又痒,抠了又痛……”
“你忘记我们半夜起来打着电筒捉臭虫的情景了?”战友杨瑞云一如当年被臭虫咬的样子,双手抱紧双肩,啧啧地噤若寒蝉。
怎么会忘记?我们几个(史娟娟、杨瑞云、张晓云、我等等)都住工棚的楼上地铺;因为地板太硬,就铺了一层干茅草。特别是夏天,一到夜里,臭虫就堂而皇之地游走在我们的垫絮边、被子上、蚊帐里,说一抓就是好几个你别以为是夸张。一天,我被臭虫咬得实在睡不着,打开电筒一看,妈呀!蚊帐顶上有好几处几个成一小堆的臭虫。我兴奋极了,触醒杨瑞云,爬起来就开始了“筛臭虫”。我俩相对着,两手分别揪住蚊帐顶的四个角,会心地对视一下,两双手默契地一左一右、一前一后地重复着,不一会儿,蚊帐顶部中间凹处就有了一小窝被摇昏了的臭虫。什么叫无师自通?生处“绝”境而靠自己的智慧取得成功!首战告捷的我们来不及庆功,倒头呼呼大睡,一觉天亮!当然,我们上铺几个战友的“筛臭虫”,就周而复始地重复着……
为了湘黔铁路大会战的提前胜利完成争取时间,要搬掉横亘在插旗山的一座山岭。上级领导决定采取大爆破施工。大爆破工程有17个导洞和23个药室,我们七连的任务是打通4、5、6号洞。连里的男生陈贵安、滕铁坚、赵成跃、杨永平等战友,毛遂自荐“打前站”。这个“打前站”可不是凿平地那么简单。那几位男生先在指定的山腰上开出一条从山下至山上的小路,又紧随指导他们的技术师傅,腰拴麻绳,手拿錾子,在悬崖峭壁上先錾出可以落双脚的栈道;再一人手握钢钎,一人手抡大锤,一锤一锤地凿出一个个洞的雏形;紧接着,掌握钢钎的男生配合着锤子的韵律转动着钢钎,坚硬的岩石就这么一点点地被錾成一个个炮眼。当炮眼的深度达到要求时,将炸药塞进炮眼,把引线牵到洞口;班长叫所有人都远离该洞,进入另一个权当掩体的洞里;然后,手里擎着旗语的战友王应荣旗子肯定地一挥,班长点燃引线,三步两步跑到另外一个洞里掩藏;大家双手蒙住耳朵,约摸几秒钟后,只听得嗡的一声闷响,大家欢呼起来,这次推进洞深度的爆破又告成功。后来有了“风镐”,钻洞的战友们就没有这样辛苦了。但是,安全隐患无时不在。
战友陈贵安想起他50年前差点就“报销”在洞里的情景:
“当每个装炸药的洞深度达到标准时,班长招呼大家撤离;班长点然引线、将引线牵到洞口后,亦是即刻撤离。但,班长在跑出洞之前还有一道工序,就是将洞里照明的电灯泡以及电线一起带出洞。有一天,我点燃了引线,在取挂在洞顶的电线时,手拇指触到了一根裸露的电线头,顿时我就被打晕倒地,什么也不知道了!幸亏罗(朝富)指导员机灵,随手拿起木棒一棒就打断了电线,我竟然一个激灵就站了起来;罗指导员拉上我就跑,刚跑出洞口,洞里就爆炸了。我以为我不死在洞里,也会落得个残废了呢!罗指导员是我的救命恩人哦!”
无独有偶,亦是在山上打洞的工作中,另一个班
长赵成跃说出了他最难忘的一个镜像:
“由于打洞时很热,我们的外套一般都是随手丢在洞中自己站位的随便一个地方。一次,因为已经点燃了雷管的引线,我快步跑出洞口,才想起我的外套没有拿出来,要回去拿已经不可能了。随着“轰”的一声,只见我的外套随着爆破后的小石块、尘土,一起冲出洞口,飞落下山……那可是我唯一的一件外套啊!”
50年后,赵成跃说起他那件飘逝的外套,还是满满的惋惜。
“可惜我连大爆破都没有看到!”停了一歇,没有收回眺望远方的赵成跃,迷蒙着双眼,莫不遗憾地说。
一石激起千重浪。战友们争先恐后、相互“翻阅”着自己在湾溪修建湘黔铁路的青春一页。
我们七连的伙食,是驻扎在“威虎山”的二营六、七、八、十连中最好的。这得益于我们有幸遇上了几位好的连领导,特别是梅影指导员。
“一定要让学生们至少每个星期吃上一次猪血。他们在山上打洞,天天都会吸入一些灰尘,猪血进入肠道,可以裹走一些灰尘。”所以,炊事班一再进城(凯里县城)努力踅摸猪下水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连会经常吃到猪大肠、猪血旺。
梅指导员每天上工,总是走在部队的尾巴殿后,总是能细致入微地关心到每一个他湖北腔里的“雨生(女生)”。完成大爆破工作之后不久就过年了。过完年,我们的新任务是每天到清水江捡鹅卵石敲道砟,这工作一直持续到1972年10月铁路修通。其中,赤日炎炎、汗流浃背的七月流火,是我们在工地上最难熬的日子。
一天下午,刚走在远离连部一公里处去捡鹅卵石的路上,我突然肚子阴痛起来;开始我还能忍着,谁知肚子越走越认真地搅痛开了。我痛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出列,蹲在地上,想缓缓疼痛再站起来接着走。这时,梅指导员走过来,问了我是怎么回事,我就说肚子好痛;说着,汗水、泪水一起滚了下来。梅指导员看了看我,轻声地说:“脸色很不好哦!能走吗?(我点点头)回去休息吧!”我又害羞又惭愧地一步一挪地走回连队。这事过去大约三两天吧,在开完了每周总结会的尾声,梅指导员宣布,以后每个月,每个“雨”同学,可以休假一天。“雨”同学们都心照不宣地轻声欢呼起来。这时候,连里一个老坐第一排、名叫李宁的男生嬉笑着朝梅指导员询问:“为什么我们男生就没有一天休假?光是他们女生有?”梅指导员作恼怒状,顺手一巴掌敲在小李宁的头上。全连“哄”地一笑,散会!从此,全连女生就有了约定俗成、不用说明白的每月一天休假;从此,梅指导员就得了个绰号“老父亲”。
多好的“老父亲”啊!虽然小李宁是一句玩笑话,但“老父亲”认真了。大约三天后,全连战士的作息时间有了调整:上午8点工作到11点,下午5点工作到8点半收工,迈开了黔东南大山里最高温的12点至16点的酷暑三伏天。
每天收工回到连队,大家吃完晚饭,戏水游泳、结伴散步、扎堆聊天,是连里战友们的常态。喜欢读书的呢,就会回到工棚读书或者抄书。我的《马克思给燕妮的诗集》《欧根•奥列金》《少年维特之烦恼》《唐诗100首》《宋词注释》等书,都是那时候在七连二排的工棚中、蚊帐里,透过工棚中央、放置一个上下木楼梯不足80公分空隙而共同分享的一盏微弱的灯光,半躺在蚊帐里、只露出头,在晚上10点钟关灯以前,辗转借来读(抄)的。现在想起来,那时为什么不给我们安置两盏灯呢?为节约用电?不得而知。
三
噢!我们不会再有一个50年了。绿皮火车呀,你慢一点,再慢一点慢一点吧!让我们再一次聆听50年前还有些许生疏、隔膜,但天天同饮一江水、同吃一锅饭、同住一工棚、同修一条路的年轻战友,今天两鬓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们一遍遍重复的絮叨吧!这可是别人不理解、可他(她)们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集体花季啊!
还记得本文开头,亦就是50年前我大哥送我上大客车时递给我的那本小书吗?对!那是《马克思写给燕妮的诗集》。就用诗集扉页上那首1836年18岁的马克思写给22岁燕妮的诗当作50年后湾溪重聚之念想吧——
我永生不能将你遗忘
咱俩永远对对双双
你在我的心中 心中 心中
就像玫瑰长在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