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指鹿为马”纵横谈,从政治权术到文化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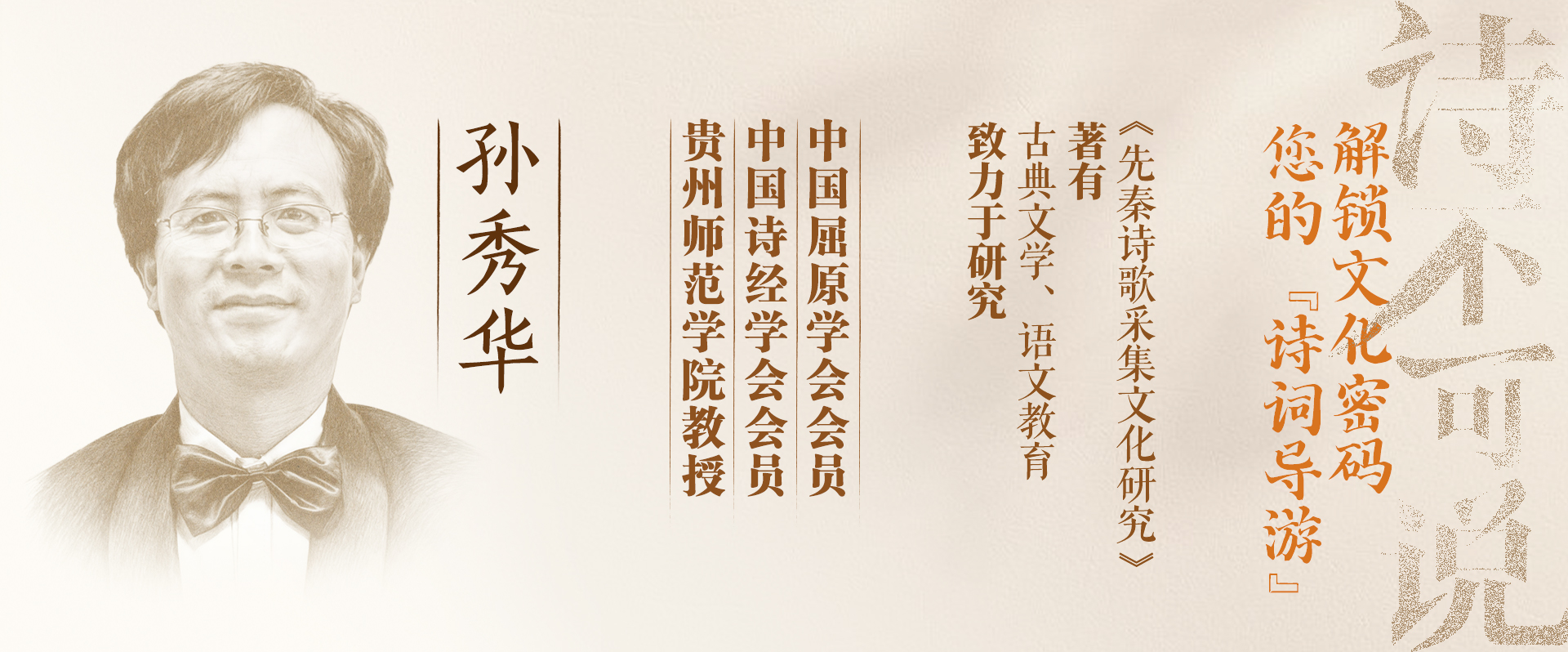
马年快要到了,本专栏将陆续谈谈与马相关的几个成语。本期先从知晓度较为“小众”但其历史地位却又极其重要的“指鹿为马”说起。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曰:
(秦二世三年)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按照专家推算,秦二世三年八月己亥日,为秦历八月十二日,对应公元前207年9月12日。就在这一天,指鹿为马的闹剧发生于秦朝都城咸阳宫内,丞相赵高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胡亥,却公然宣称这是一匹马。群臣或沉默或附和或直言,这一幕看似荒诞不经,却如一块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超越了单一的历史事件,演变为一个凝聚政治阴谋、文化批判和人性反思的复合型文化符号。

赵高“指鹿为马”的行为绝非一时兴起,其真正目的有三层:表层是辨别敌友,中层是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深层则是完成一次“现实重构”的政治实验。当足够多的人被迫接受“谓鹿为马”的设定时,权力就完成了对事实的定义权垄断。
汉乐府《折杨柳行》歌云:“指鹿用为马,胡亥以丧躯。”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的对“指鹿为马”的歌咏。

唐代贺兰进明《古意》诗曰:“秦庭初指鹿,群盗满山东。”这里将“指鹿为马”这一朝廷内部的道德溃败,与外部“群盗满山东”的社会动乱直接因果化,暗示上层失德必导致天下大乱。
唐代于濆《秦原览古》诗曰:
耕者戮力地,龙虎曾角逐。
火德道将亨,夜逢蛇母哭。
昔日望夷宫,是处寻桑谷。
汉祖竟为龙,赵高徒指鹿。
当时行路人,已合伤心目。
汉祚又千年,秦原草还绿。
诗作主旨是在遥想当年龙虎斗,伤心秦汉经行处。而“赵高徒指鹿”,“秦原草还绿”,无限惆怅情,桑谷望夷宫。
唐末周昙《秦门·胡亥》诗云:
鹿马何难辨是非,宁劳卜筮问安危?
权臣为乱多如此,亡国时君不自知。
如此语调,心系国之安危,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的批判。安史之乱后,形势急转而下,唐朝中央权威削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士人们自然联想到秦末乱象,亡国之忧,忧君之痛,痛恨愤懑,无不彰显。
北宋王安石在《桃源行》中写道:“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王安石对“指鹿为马”的思考更加内向化、哲理化。作为改革家,他对政治运作的复杂性有更深体会,而权力的自我腐蚀似乎永无止境。一旦“指鹿为马”发生,则会立即产生“秦人半死长城下”的恶果,这足够让人警醒。
南宋王十朋《咏史诗·其十九·二世》诗曰:
始皇一怒逐扶苏,天欲亡秦果在胡。
翻被四方黔首笑,不分鹿马是谁愚。
“翻被四方黔首笑”,秦二世而亡,为天下笑。西汉贾谊《过秦论》有曰:“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贾谊进一步分析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失去民心的政权终将崩溃。故而,“不分鹿马是谁愚”,当“谓鹿为马”在庙堂之上赫然发生,政治忠诚、政治品德早已无从谈起,又岂是智慧与愚蠢的问题呢。
明代申钦《鹿马叹》诗云:
无角者马,有角者鹿。
无角有角,有目皆瞩。
言鹿者祸,言马者福。
鹿马不辨,鹿亦终逐。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当“鹿马不辨”,祸害必将危及国运。覆巢之下无完卵,唯有政治清明,才能天下大安。
显而易见,“指鹿为马”之所以能迅速成语化并进入文化基因库,源于其高度凝练的象征性。这个典故在随后的两千两百年间被反复征引,每一次引用都是一次现实批判或自我警示。“指鹿为马”成为一种文化“快捷方式”,无需冗长解释即可传达“权力扭曲真相”“多数人的暴力”“知识分子的失语”等复杂命题。

为政必先“正名”。《论语·子路》载孔子论述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而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命名与本质的关系一直是核心议题。柏拉图认为名称应反映本质,亚里士多德强调分类的重要性。因此,西方文化中对“错误命名”尤为敏感。莎士比亚的名言“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出自其经典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原文为“What's in a name? 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word would smell as sweet.”直译大致是说:名字代表什么?我们所称的玫瑰,换任何名字还是一样芳香。从哲理上理解这句话,其实是通过玫瑰的比喻,探讨了名称与本质的关系。而从同样的理性分析,则不难理解与接受“指鹿为马”的暗示:当名称与本质分离,秩序必将陷入混乱。
现今西方世界最为人知广受喜爱的“以鹿为马”的案例当然就是圣诞老人的驯鹿雪橇了。尽管拉雪橇的到底是哪种鹿,仍有麋鹿、驼鹿还是驯鹿之争,但总归支持驯鹿说法的为多。且这一“争议”的存在本身,也便说明了圣诞老人故事的持续生成性。你知道吗,圣诞老人雪橇车动力来自九只会飞的驯鹿。而领头的那只叫鲁道夫,又称红鼻子驯鹿鲁道夫,是圣诞传说中为圣诞老人拉雪橇的第九只驯鹿,由美国作家罗伯特·梅于1939年为安慰患病妻子之女创作。其形象因发光的红色鼻子成为圣诞故事核心角色,后经1949年同名的圣诞歌“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的传唱,传播为全球性文化符号。
中国还有“真以鹿为马”的民族风俗,且早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7日,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申报的鄂温克驯鹿习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王郑胤 摄
王郑胤 摄
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驯鹿被作为“林海之舟”,鄂温克人赋予驯鹿类似马的功能,用以骑乘、驮运、拉车。鄂温克语中,驯鹿被称为“鄂伦”,意为“陪伴者”。这种命名不是权力的强加,而是基于长期共生关系的自然生成。驯鹿适应寒带苔原的宽大蹄掌,在鄂温克人生活的沼泽、雪地中比马蹄更有优势;它们以苔藓为食,不与人争粮;性情温顺,易于驯养。在这里,这种“功能性的指鹿为马”,基于实际需求的“功能性替代”,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而当代鄂温克人却也面临着一个反向的“指鹿为马”困境:外界游客、媒体、学者常常将自己的想象强加于他们的驯鹿文化。驯鹿被浪漫化为“圣诞老人的坐骑”“神秘的森林精灵”,而鄂温克人则被定格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始部落”。这种外部强加的标签,本质上也是一种“指鹿为马”——将复杂的文化实践简化为满足外界期待的刻板印象。
穿越两千两百多年的时光,从秦宫殿到唐诗宋词,从希腊神话到鄂温克森林,“指鹿为马”的故事不断被重述、重构、重新诠释。今天,当我们讨论“后真相时代”“假新闻”“认知战”时,本质上仍在回应“指鹿为马”提出的古老问题,当权威声音与感官证据冲突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当多数人都接受某种叙事时,少数人的坚持是勇气还是顽固?
在终极意义上理解,“指鹿为马”的悖论暴露了人类认知的根本困境,而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困境中,不是面对一只被称作马的鹿,而是面对无数被权力、利益、意识形态重新命名与文化持续构建的事物。而当我们再次读到那些引用这一典故的诗词,或是听闻远方民族与驯鹿的故事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关于真实与虚构,关于权力与抵抗,关于命名与本质。这场对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迫切,而唯有始终坚守内心的真诚,才能给出顶天立地的坦坦荡荡的正确答案。


